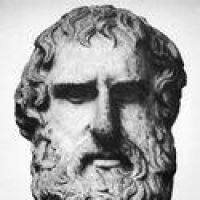舍尤素夫
/文学
夜空,也有两只眼睛……
作者:舍·尤素夫[东乡族]
暮色四合。村庄、树木、山岗、小路都渐渐模糊了,黯淡了,黯淡得连它们的轮廓也无法辨清。深邃而辽阔的天空中,一群群的星斗,不知从什么地方蹦了出来,明明灭灭地忽闪着,显得顽皮而又活泼。相形之下,拿拉图村上空悬挂的那弯新月,却面对群星,黯然神伤。它那镰刀般似露非露的脸儿,如果不是拿拉图村青年妇女细腻的、敏锐的、在夜的灵气里经常凝睇的眼神的话,一般肉眼几乎看不出来。 其实,阴历九月二十一二的晚上,月亮还没出来呢。那不是一勾新月,而是拿拉图清真寺礼拜大殿顶的宝罐铁杆上装饰的一个象征,一块新月型镀银不锈钢片。 她,祖丽哈正倚在自家的大门框上,仰目凝视着那一勾新月,心里浮上一缕淡淡的忧虑:这么晚了,她的男人尔利穆还没有回来。 隔壁新修的一家院里,传来一个女人嘤嘤的哭泣声,更增添了秋夜的凄迷和冷清。她,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噤,双臂交叉地抱住了自己的肩头。 她的男人——尔利穆,是拿拉图村的贩运户。他先是承包了队里的一台手扶拖拉机,后来干脆自己买下了。每一集从尕扎镇上的集市籴进绿豆,装满一拖斗,尔后再到河州城粜出去。尕扎镇上的豆价是二毛五六,到了河州就可以粜它个二毛八九,运气顺了,三毛挂头。河州城里那些集体和个体户粉条作坊,都是他的主顾,他和他们都混熟了。熟人们问他:“你这一趟能捞多少钱?”尔利穆总是诡谲地挤挤眼睛:“一斤落个一分吧,刚够个运费钱,有点划不来,拾个馍渣渣罢了。”一斤一分钱,两千斤就是二十块,除去柴油和其它交费,剩个十头八块,也不错呵。其实他每斤上头,可以捞三至四分钱,三天一个来回。头一天赶尕扎集籴绿豆,第二天跑河州,第三天返回拿拉图村,除去交费,净挣四十多块,一天十多块没问题,他怕有人拆他的行,所以总是保密。他贼得很,不得不说时,把数字保守到最低的档档里。就连自己的老婆也不告诉。而老实憨厚的祖丽哈也从来不打听,她总是忙不完家中里里外外的活。 拿拉图村子的人都知道,他们村里已出了两个有钱汉,一户是隔壁一家,一户是尔利穆家。 年轻的媳妇们有时候碰到一起,也常跟她开玩笑:“祖丽哈阿姐,你们尔利穆都挣了大钱,你怎么老是这个样儿呢?” “不这个样儿又能咋个样儿呢?”她也笑嘻嘻地问。她们努努嘴:“看看你隔壁家的茹茹,你没见她一天一个样子,穿得多显,比新媳妇还嫩气呢。” “我可没有茹茹那个福命哟!一天少挨打就知感的很了。”她们都知道她男人原先打过她。 “你还怕他打呀?”媳妇子们洒下开心的笑,各忙各的去了。如今这年月,女当家们最珍惜光阴,瞎扯闲聊的时候是不多的。 有时邻居那个贵气的茹茹也过来到祖丽哈家坐坐。茹茹是村里最清闲的一个女人,家里的责任田早就退了,在家里享起清福来,——两只手横草不拿,竖草不动,保养得白白胖胖。女人们太清闲了,就会生出寂寞来,寂寞又养出饶舌。她时不时地过来给祖丽哈炫耀本事:“我才不当那个大头,我们那口子外头散舒了个美,我给他苦死苦活?哼,没的事。你呀,”茹茹手指着祖丽哈,说:“真笨,不会享福,你们尔利穆把钱都干啥去了?会不会藏起来?”祖丽哈一听,觉得好笑:“藏起来干啥呀?” “干啥?哼!有了钱的男人们可坏着呢,他不会拿钱在城里娶个漂亮的尕奶奶(注:尕奶奶:方言,小老婆。)。” “娶尕奶奶?格格格……”祖丽哈用手背捂住嘴,忍不住笑起来。 “笑什么。我们那口儿,杂疙瘩(注:杂疙瘩:方言,骂人的话,杂种。)偷偷摸摸在城里就娶了个尕奶奶,你不信?”祖丽哈似乎从别的女人口里也曾听说过这么件事,似信非信的,她看看茹茹怅然的表情,疑惑地问:“不会吧,他娶了尕奶奶,会管你这个家吗?”“不管?他敢。我到法院去告他。杂疙瘩。”茹茹愤然大骂自己的男人,两句话还没骂完,火气又消失了:“娶就娶吧,管他呢。反正有我吃的,有我花的就行了。哎,你可小心呀,你们那个尔利穆,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祖丽哈心里格登一沉,脸上老大一会的不自然。 “哎,别再想了,到我们家看电视去。那玩意儿,可真有意思,有时,男的女的在亲嘴儿,嘿嘿,怪不得现在男人们一出门就变坏。”茹茹强拉硬拽把祖丽哈弄到自己家里。 茹茹家里摆设阔得要命,三大间出椽雕花的大瓦房里,叫不上名堂的明晃晃、亮晶晶的各种高低柜子、沙发,满满的摆了一地,乡村的人乍一坐在这样的房间里,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种拘谨感。怪不得昔日里来往过密的媳妇子们,与茹茹来往日渐稀少了。 祖丽哈坐在软乎乎的沙发椅上,心里颤悠悠的,浑身不自在。她眼睛盯着屏幕,也没有见着一个亲嘴儿的。茹茹虽说瞧着电视,可嘴里哇啦哇啦地光诉说她的心事,一会儿浪笑,一会儿叨叨。她,这个清闲无聊的女人,心思不知放在什么上。 自从那回看过电视没多久,安享清福的茹茹家里出了事儿了。他的男人给河州城一个倒卖黄金白银的大走私犯当“脚户”(走私行里的黑话,掌柜出资找货,他跑广州,算伙计之类吧),原先与掌柜四六分成,跑了几年,自立门户了。后来在南方某城市跟一个港客兜揽生意时,被公安局当场抓获,连本烂了不说,人都抓到县里来了。听说要判十年左右徒刑。男人的黄金梦破灭了。茹茹这个“贵人”坐享清福的天份也被一阵风卷跑了。养得白白净净,穿戴花花绿绿的茹茹好不伤心,时不时恸哭一阵子,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像一种无形的恐怖,攫住了祖丽哈的心:自己的男人,贩绿豆的尕车户,会不会遇到突如其来的熬煎?啊,这个,除非全能的真主知道。 祖丽哈长久地倚在门框上,仰目凝视着清真寺上空的一勾隐隐约约的新月,心里默默地祈祷着:胡大呀,请襄助我的尔利穆平安无事吧。 此时,高高的姆拿拉上(注:清真寺的高塔。),一个头缠太斯达日(白色的头巾)的满拉哥(清真寺里学经文的人)沿着旋梯,攀缘而上,在塔顶上訇然有声地诵念着班克(箴词),呼唤着前来做礼拜的虔诚者,他的声音在夜空里颤响了很久。 和呼坦(注:掌灯时分。)时辰到了,巷道口里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那是村里的男人们到清真寺去做昏礼。祖丽哈很快虚掩了大门,闪进家里。她怕村里人见了笑话,都快半茬子了,还这么痴情,怕自己的男人被谁抢走似的。 老大一会,尔利穆回来了。这一次,听不见他那手扶“突突突”报讯的声音,他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回来了。 “给,你试试看。”一进门,他故意把语气放得极为平淡,在自己妻子的身后,掩藏住一种微妙的情绪。其实,他此时的心情是销魂惬意的,满以为妻子会为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惊讶。 “什么呀?你让我试什么呀?”祖丽哈也背着身子,从三格子大板柜里拿簸箕取小麦,准备筛簸干净以后,明儿,一大早就到磨房去。因而有点漫不经心,连头都没回一下。尔利穆一听,心里很不高兴,说得过火一点,简直是大煞风景。“你穿不穿?”他有点愠怒,“不穿拉倒,我干脆送人了。”这话毕竟带一点刺激性,她倏地转过脸来,两臂依然伸到柜里取粮食,疑惑地看着丈夫手里一套折叠得齐整漂亮的深蓝毛华达呢衣服,和一双女式红高跟鞋。“给谁买的?让我试着干啥呀?”自从她过到这个家里,他从没亲手给她买过一件衣服,今天是头一次,也许是头一次吧——因此,祖丽哈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她这不疼不痒地一问,倒使尔利穆冒火了,竟破口大骂起来:“像你这号人,生就是挨打的下家。”他气得有点结巴,下面的话立刹里接不上茬了,顿了一下,又想起了一句,嗓门高了八度:“白吃萝卜还嫌辣哩。”一怒之下,把手中的衣服和高跟鞋扔到炕头上,扬长而去。他们夫妻间,尤其她,已经习惯于丈夫这种粗暴鲁莽的态度了。那种缠缠绵绵的柔情,她还很少领略呢。祖丽哈拍打着双手,拣起衣服,以女人特有的细腻,细细地看了几眼,把头探到屋外,喊:“这是从哪儿买的?”他听都不听,径直出了大门。她这才慌了,猛想起丈夫从一大早进城,回家来还没有吃饭呢。 她“咚咚咚”地跑出大门外,冲他背影喊道:“你上哪儿去?我把饭都做好了。”没有回音,尔利穆沿着深深的巷道口,扬长而去了。 院子里,不知啥时候,一片淡淡的月光撒了一地,像是撒了白霜的秋晨,显得那么静谧。 她,捧着衣服,心里着实有点纳闷。咦,他今儿个上城,我并没有托他买衣服呀,这是谁告诉他的。再有一个月,她娘家的三妹就要出嫁了。三妹是她姊妹中唯一有文化的人,去年念完了高中,没升上大学,家里待了半年,父亲就找了个主儿,想把她早日嫁出去。“女大是祸,不能多拖。”乡旯旮里自有乡旯旮里的规程。三妹不太情愿,不情愿也得嫁,在这乡间情情愿愿自由结婚的有几个人?娘家的兄弟大前天到她这里报讯,还向她请了“仲卜拉”(注:仲卜拉:特制的一种油花馒头,很大,通常一个有十斤多重,是东乡族婚礼上的专用食品。),并请她早一点儿回娘家,帮扶帮扶。她兄弟来的时候,她男人尔利穆不在家,之后,她也没把这事儿告诉丈夫。原来,她不想告诉他,她想一个人偷偷地去。反正,如今这酥油年间里,她是“管家婆”,家里小麦有的是,“仲卜拉”也愁不倒人了。娘家的妹妹结婚,这本来是当姐夫姐姐的一件大事,那么怎么不让他知道呢?这里面难道真有点难言之隐?有,不过她极不愿意想起那桩事儿。说起来也怪,那前嫌还是和这衣服有关呢。 七年以前,她的二妹妹出嫁了,请她当“苏还赤”(注:苏还赤:东乡语,送亲的伴娘。女子结婚,一般由姐姐和姑姑当伴娘。)当苏还赤,她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整天风里来,雨里去,身上穿的一件外套,还是那一件紫红条绒的斜襟衣服,这还是当新娘时穿的呢。无奈,她怯生生地告诉了丈夫。尔利穆是个脾气暴躁而又不怎么管家的人,且对嘴上抓揽的又紧,经常在外面偷吃了“平伙”(平伙:东乡族习俗,十几个人搭伙吃全羊。),讨账的人就接踵而至。没钱还账,挖你柜里的包谷抵账。一顿肉就能吃掉五六十斤包谷,为这事她常和丈夫吵架,结果总是被丈夫“武力解决”,打得她鼻青脸肿。她为此没少哭过鼻子,跑到娘家不想再回来。可父亲总是息事宁人,让她最多住上三天就送回来了。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说父亲是怕家中缺粮,勒紧肚带的日子,一斤口粮可要人的命哩。扯一件衣服,可怎么向丈夫张口呢,连他一身的债务都是由填她肚子的包谷来支付的。于是,她狠了狠心,说通了丈夫,又向一家人的口粮下手了,跑到自留地里,忍疼挖了一大口袋洋芋,七八月的洋芋,自然没有长好。一口袋洋芋,挖了偌大一片地。为二妹的婚事,她也顾不得饿肚子的威胁了,苦苦哀求着向队长借了一头驴,叫丈夫驮着洋芋到河州城粜黑市(那时把自由市场叫黑市)。粜了以后,好扯一件好料子回来。那一天她下工回来,天上悬着一弯模糊的月亮,她盼着他早回来。做熟了包谷面散饭,又在炕灰里烧了一琼锅洋芋,并烙了几张包谷面煎饼,还炒了一碟子洋芋菜。当时按她所操持的家务条件,这算是最丰盛的晚餐了。她,一忽儿出了大门,一忽儿又踅进来。麻糊子月亮一直躲在云彩里不出来。她引颈翘望村头的小路,倚在大门门框上,心情说不上是爽悦还是有点凄楚。 刚三岁多的娃娃哭喊着不依,她抱着尕娃娃上了炕。大门一直开着。一天的农田基建活儿的确叫她疲惫不堪,一阵困扰袭来,她在枕头上打起迷盹来。 门吱啦一声响了,她惊醒来,原来是男人回来了。她利手利脚地下了炕:“怎么这么晚才回来?饭都凉了,我给你热热去。” “不吃。”他冷冷地说,用困惑的目光看了她一眼,无精打采地从炕沿上的米谷草穗的小扫帚上摘了一根草棍,剔起牙来。那模样儿,像是吃饱了肉的阔佬在闲散得无聊。 “在哪儿吃的饭?” “……” “一点儿都不吃吗?我都给你烧的琼锅馍。” 他只是用草棍剔着牙,怎么也不回答。时而翻翻眼珠,摆出一付丢了羊羔的牧童愧惶惶的样儿,又像是市井无赖的架势。她似乎预感到了什么。 “买的衣服来?”她眼睁睁地瞪着他。 “你买的衣服来呀?”她有点着急了,眼光在屋子四周睃巡搜寻着,舌头已有点打颤了:“你怎么不吭声?” “噗。”他很利落地把剔牙的草棍狠劲地吐到地上:“粜什么洋芋,叫那些市管会的家伙撵得像兔一样,这里藏藏,那里猫猫的,要不是碰见一个老熟人,今天进城连一碗汤也喝不上。”他有点愤懑,把脚一伸,圆口鞋叭哒一声掉在地上,便心灰意懒地上炕了。 “那我怎么去当苏还赤呀?”她急得差点哭出来,妹妹的婚期就到了,她,当大姐的就这么去臊脸呀。 “当什么苏还赤,你就别去了。”他一面说着,一面十分困乏地躺下了。一会儿便轻轻地打起呼噜来。她定定地看他的样儿,这才想到丈夫的脾性来,粜洋芋的钱一定是叫他在城里的黑市馆子里打了牙祭。她猛地爬在炕沿上,失声哭起来:“我怎么嫁了这么个没出息的男人呀,唔唔……”越哭声音越大,越哭越伤心。卖鸡吧,没鸡,卖羊吧,自留羊早就收走了。 “你嚎什么?!尿尿多了上茅坑去。”他在困顿慵懒的迷糊中乍醒,满脸的厌烦。哭声倒愈加恸楚了:“呜呜,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哩……” “我不要脸咋了?”一个巴掌甩过去。他感到冤枉了,进城惹了一肚子臊,几个戴红袖标的人,把他追到一条死巷道里。粜不出去,干脆他叫一个熟人引着,一口袋洋芋换了一顿肉。这总比让那些如狼似虎的“红袖标”没收强一些。可是回到家里也遭冤。他又打起老婆来。 她把头一个劲地往他怀里撞:“今天你打死我吧。你连狗都不如,狗嘴馋了,还拿舌头舔石头呢。”对丈夫,这一次她把最难听的话都骂出口来了。 当完苏还赤,她赌气着,赖在娘家里不想回来了。可给别人又不好启口说自己的男人没出息,住了一晌,父亲又把她送回来。 自那以后,家里需要什么,她从来再不求丈夫去办了,而宁肯偷偷地托给别人。她也开始瞒着男人,攒开私房钱来。其实那时候,穷的叮当响,她一个山沟里的妇道人家,哪有什么私房好攒的。只不过是线头布头的零物罢了。唉…… 可今天这是怎么啦?她压根儿没要什么呀,他就给她买来了,心里真有一种甜丝丝的感觉。结婚十年了,自己这没出息的男人从来还没有给作妻子的买过一件衣服呢。祖丽哈时而手摩挲着高级的毛料的衣裤,时而新奇地瞧着那一双红牛皮高跟鞋。乡间虽说现在情况好的多了,可穿高级毛料、高跟皮鞋的人还是比较少见。只有隔壁的茹茹,他男人都给她买全了。原来并不起眼的茹茹,穿上了,人前人后好贵气呀。 祖丽哈似乎隐隐听到茹茹咬着被角,嘤嘤地哭泣。突然,她心里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但又经不住一种新物的诱惑——毕竟是三十挂零的女人,心的角落里,没有泯灭的东西还多着呢。她回到屋子里,把那套衣服真的试了试,穿在身上。嘻,这大翻领,怎么胸前露出这么大一块下面的旧衣服来。她赶紧又把前些天自己买的那一件粉红色的毛衣,从箱子里抖出来,穿在下面。这件粉红毛衣,她是喜慕了几年,谋算了几年的。临买的时候还犹豫了一阵。这毛衣姑娘们穿上的确好看,她,已经三十岁了,已成了山沟里的“老媳妇”了,穿上怕不合适吧?但她还是买了,只是怕人家笑话。一直没有穿出去。今晚儿,她都穿上了,站了起来,浑身一看,一种突如其来的颤栗,从头震到脚上。腿上那直楞楞的裤线叫她心里扑扑直跳。还没来得及在灯下往镜子里照上一眼,扎着小辫辫,钻在被窝里睡觉的小女儿忽地坐了起来,拍着手嚷开了:“阿娜要当诗尼别勒(诗尼别勒,东乡语,新娘子。)喽,阿娜要当诗尼别勒喽!”她顿时像被烤得通红的灶火门,脸上烧得红红的:“嚷什么,你再嚷当心阿娜撕你的嘴。” “哎勒勒勒,阿娜娜要当诗尼别勒哩,阿娜要当诗尼别勒哩。”小儿子也爬起来,嚷得更厉害了。她慌乱地脱下来,一边竭力顺着线儿叠起来一边朝着儿女们说道:“别嚷嚷,这是你阿达给你们尕姨娘买的,你尕姨娘过一个月,才真正当诗尼别勒哩。” “阿娜,尕姨娘当诗尼别勒,我要去吃筵席。”一儿一女轮着又吵开了。 “我才不引你们去,刚才你们胡喊啥。” “阿姐先喊的,我没喊,我没喊。”小儿子倒挺乖巧,把责任全推给小阿姐。小姐弟俩开始斗开嘴了,吵得不可开交。 她扑嗤一声笑了,笑得怪甜:“别吵了,别吵了。都给我睡觉,谁先睡着,我就引谁去。” “我先睡着了。”小儿子钻进被窝里,使劲闭着眼睛,小脸蛋皱成一个毛线团。 “我先睡着了。”女儿用被窝捂起脸,两只手紧紧地捏住被头。 她好容易顺着褶儿,原打原样地叠在一起了。请别笑话,这也不是什么羞于说出口的,新式样的衣裤,以前就是没叠过嘛。 “你们两个再胡动,我真的不引了。” 被窝里一阵??作响,两个小宝贝闻声吓得再不敢动弹了。
她,出了大门望了一会儿,心里始觉得有点懊悔。今晚似乎不该叫他的一片热心受到冷落,可这怪谁呀,谁知道这料子衣服是怎么回事。她又想起隔壁的那位茹茹来,一种莫名的怅惘袭上心头,顿时叫她的心情慵恹恹的。她把那一套衣服推到炕脚头,熄了灯,和衣躺下了。 此时,窗外那溶溶的月光,从门缝子里偷偷地溜进屋子,似乎在偷听她的叹息——她那心灵深处微弱的叹息。 迷迷蒙蒙中,门一推,响声好猛。他就是这么个人。 “起来起来,你倒舒服,吃完饭就睡觉。”他把粗壮的手臂伸过来,想摸她的脸。“我还没吃饭哩。起来起来。”
“饿了你自己做,半夜三更的在哪家门口浪三浪,我不起来。”她一翻身,侧过脸去。 “嘿,浪的时节早过去了。”他一把把她拉起来,把个黑纱绒盖头,白帽子都给扯了下来,黑油油的头发披散在她的肩上。 “真的,我还没有吃饭哩。”说着他把手就往被窝里塞。 “别胡闹,娃们刚睡着。”她利索地下了炕,捅开铁炉子。 “刚才你,你——”她顿了一下:“你咋走了?” “咳。有事呗,给村委会主任交了个申请,责任田咱不种了,咱转包给别人。” “不种?咱吃什么。”她听了非常惊骇,疑惑的目光在他脸上游移着。不知为啥,她想到茹茹。 “饿不着你,放心。咦?”他的目光移到炕柜上,又突然记起了什么:“那套衣服你试了没,合身不?你再穿上,我看看,看我的老婆漂亮不。” “不穿,我老了。那么漂亮的毛料子,要试,找一个年轻漂亮的给你试去吧。” “你胡说什么呀,再胡说,看我揍你!”他真粗鲁地挥起拳头来。她,想笑又没笑出来:“非得夜里穿?” “当然。” “为啥?” “当城里人。我在城里花了大本钱,买了四大间铺子,开个大绿豆店,你当老板娘。嘿嘿……”他拿指头掠着她的脸颊,乐得把嘴裂得好大:“你当掌柜的,我给你当下手,找货跑运输,怎么样?” “别没正经的,胡开什么玩笑。” “谁开玩笑啦,连你都不相信,我尔利穆就要叫人们大吃一惊,狗日的。”他瞪大眼珠子,唾沫星子乱溅,显得好不得意:“明儿,我引你领营业执照。领营业执照,人家说要像片,你连一张像都没照过,亏人。咦,你见过照像的吗?”他很得意,比比划划地做着样子。“咦”他一眼?见了斜躺在柜底下的高跟皮鞋和毛料子,顺手拿起来,眼光火辣辣地逼视着她:“你穿不穿?不穿我把它扔到火炉里去了。” 她,十多年了,知道这个鲁莽家伙的火爆性子,一不顺心,说得出蠢话,也能做得出蠢事,不能再折他的面子了。她笑咪咪地,给了他一个媚眼,伸出手,嗲声嗲气地嗔了一句:“拿来!” “嘿儿……”他捂着嘴笑了:“女人,小心眼,怕了就成。咳,其实呀,不穿不行。咱这山沟里,你穿啥,没人嫌。可城里不一样,长得都是斜巴眼,溜来溜去直瞧人家的衣服。穿得不像样,连话都搭不上,还当什么老板娘哩。” 祖丽哈把毛料衣服、高跟鞋都穿上了。这一下娉娉婷婷,秀模俊样,比城里人一点不差。这身装扮,再戴上一顶墨绿色的纱绒盖头,别有一番风韵。他呢,给她这边扯扯,那边拉拉,摇过来摆过去,弄得她怪不好意思的。 “嘿嘿,人是穿着马是鞍,一点不假。明天再抹它个半斤雪花膏。狗日的,我叫他城里人也瞧瞧。”他眼睛盯着妻子,半天合不拢嘴。 “进城真的叫我当掌柜的?” “你咋总不相信。” “可我认不得字儿,记不了账。” “不怕,我雇了一个管账的账房先生。” “账房先生?谁啥?”她显得有点忸怩。 “谁,反正是自家人。” “自家人?”她感到紧张,几乎是屏住气在问。他见她表情有点异样,突然感到有点陌生:“你是怎么啦?眼睛里带着邪火。” “那人是谁,你不说,我不去。” “又不是男人,连长相都和你一样。” “什么?”祖丽哈惊呆了,她想起茹茹在耳边捣咕的那句荒唐的话,差点气晕了。她很快把衣服脱下来,扔在炕头上:“我不去,我也不穿,你再别回家来,跟你雇下的女账房先生一块过去吧。” “你让我和谁一块过去呀?傻瓜,那账房是你亲妹妹。” 祖丽哈一下怔住了,是呀,妹妹中学毕业没事干,阿爸要她嫁人,她不干。这下可真好了,妹妹和自己可以一块儿开铺面了。 “噗嗤”一声,祖丽哈咬住嘴唇笑了。一颗晶莹的泪珠跌碎在他的手臂上。 “哎呀呀,真是一涨一落沟里的水,一上一下女人的心。我的话还没说明白,你就连汤带醋一壶灌,我算把你们服了。” “我妹妹……” “你妹妹从你娘家去河州,明天见了你自己问她吧。睡。”他一上炕,很快又拉起舒适而均匀的呼噜来。她呢,可没有睡着,心,飞到了玻璃窗外面。一弯下弦月,此时正和寺顶上的一弯新月遥相成对,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弯勾勾的,真像人的一双眼睛。只是那一只眼睛向人散溢着脉脉含情的明澈目光,谁见了,都会为之敞开那久已闭锁的心扉的。 而另一只呢?……
- 冀教版小学英语五年级下册lesson2教学视频(2)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泊秦淮》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辽宁省
- 沪教版牛津小学英语(深圳用) 四年级下册 Unit 7
- 苏教版二年级下册数学《认识东、南、西、北》
- 外研版英语七年级下册module3 unit2第一课时
- 北师大版数学四年级下册3.4包装
- 第8课 对称剪纸_第一课时(二等奖)(沪书画版二年级上册)_T3784187
- 外研版英语三起6年级下册(14版)Module3 Unit1
- 青岛版教材五年级下册第四单元(走进军营——方向与位置)用数对确定位置(一等奖)
- 外研版英语三起6年级下册(14版)Module3 Uni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