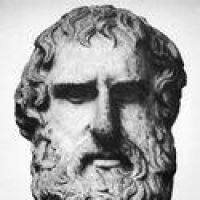祖农哈迪尔
/文学
锻炼
作者:祖农·哈迪尔[维吾尔族] 万素夫·赫捷耶夫 译
一 麦提亚孜的油菜比这个村子里的农民早下种了几天,所以他的油菜就在强烈的太阳光晒得人脊背烧灼的时节成熟了。不光是熟了,说得更确切些,已经过了收割期了。照惯例:农民在油菜茎杆将干未干的时候就要收割,不然,镰刀刚一挨上枯了的油菜茎,它那闪着金光的颗粒便会立刻迸散四地,造成浪费。麦提亚孜的油菜恰恰就处在这步境地了。还好,今天不管怎样总算是已经动镰刀了,那一束一束摆列成四十多个小堆的油菜,如果往紧里捆一下,只不过有三四捆蒿草儿那么一点罢了。
无论怎么样,活应该继续干下去吧!但,使这块苦闷的地刚刚喜笑颜开的那个收割者约有四个钟头以来就不见人了,他到底向哪儿去了呢?! 在这一望无垠的田野上,蒸发着蜃气,远远望去宛如湖水在荡漾,拴绊在渠边木桩上的马,也不吃不喝地在那里不停地摇摆着头,袅袅的熏风,把田野里的蝗虫的鸣声懒懒地送到远处去。而这“吱、吱”不断的叫声却使麦提亚孜感到厌烦。他虽然躲在那棵老桑树荫下避暑,可是这些显示着炎热难耐的虫声也好像故意和他为难。 “嗨!嗨!这么热,简直把一切都烧化了。”麦提亚孜嘀咕道。
落在桑树上的老乌鸦,张开了麸皮式的拙嘴,颤动着咽喉,麦提亚孜用那发着汁臭味的汗衫裹了些乱草,把净光的脊背竖贴在潮润润的草地上仰卧着。他软绵绵的体肤被杂草刺扎着,淘气的苍蝇也不断地骚扰着他。自今年入春以来,像这些讨厌的难耐的生灵、还有今天的这个炎热的天气也似乎在折磨着麦提亚孜。这一点儿也不假,就连落在桑树上的那只老乌鸦,不也曾经欺侮过麦提亚孜吗? 在半普特地里撒了半缸子包谷籽,结果只长了二十五棵包谷苗,成千成万颗谷粒哪儿去?岂不是被栖在那棵桑树上的那些祸害吃光了吗?!麦提亚孜望着那只乌鸦的颤动着的咽喉有点生气了。 “雷打火烧的掖食鬼!”麦提亚孜咒骂一句,便翻过身来伏卧在那里。
虽然他的两个眼睛因瞌睡而蒙胧着,但是,交织在他脑海里的懊悔和沉重的怅惘,还有令人难受的苍蝇的嗡嗡声,更不能使他安宁入睡。麦提亚孜口渴得很厉害,他便开始舐起他那干焦了的厚嘴唇。他活了四十多岁,生平没有遇到过像今天这样难熬的口渴,口渴是刚动镰刀割油菜的时候开始的。倒霉的是附近连点冰凉的泉水也没有。因此,他尽管喝了长满草莽的沟水和潭里的死水。
结果仍旧止不住渴,倒渴得他越发瘫软了。谁能经受得住口渴呢,应该喝水解渴呀。可是,现在连那死水也被阳光晒热了,要到大河边去,还得在烈日下走六七百米路,麦提亚孜可没有那个决心到那儿去。他悔恨自己当时不该由城里到乡村里来;他又想起了已经死去的慈爱的妈妈。因为他是个独生子,他妈妈非常喜欢他,把他娇生惯养了。
所以,在这进行农业生产的头一年,对麦提亚孜来说,是和他曾经在潮湿和阴暗的环境下面蠕动着度过的那四十年生涯差不多。他想:“为什么把我生在这多苦难的世界上呢?还不如小时死掉也就免得受这些罪了。” 这个新农民,活了这么大岁数,虽然也经常想着成个家,但没敢真的这样做过,所以当他在这样口渴的时候,也没有给他送一碗凉茶来的老婆。他也没有种地用的牛、马、犁,以及其他农具,甚至连个下蛋的母鸡也没有。他只有一把灵巧的砍土镘,和一把今天第一次用来割油菜的锐利的桑木把镰刀,以及两条口袋。
不过,他虽然没有较大的农具,可是却有村子里别家再也找不到的一些手工家具。 当你沿着村南边渠沟走去,便会看见靠在大路边的那堵倒塌了的围墙,里面杂草丛生,有五六棵果树和苦杏树,还有几株树干已经枯干而又从树根里正在抽出新芽的小桃树。你再走进院子北边的那个因外屋倒塌肢骸孤立的小屋去,看看吧:灶上安着一口生了锈的小锅,屋子中间只能容纳一个人睡的地方铺着像马垫子一般大的一块毡子。也许这块毡子原来是白的,如果现在还说它是白的,可能谁也不敢相信。因为,灰尘、污秽已经使它变成了灰褐色。
屋子里铁工工具、木工工具、鞋匠和理发匠用的工具混在一起,到处狼藉着。灶台上、壁橱里摆着破旧的铁盒子,生了锈的旧剃刀、小螺丝钉、螺钉帽盖、旧马掌和洋钉子……壁橱上还放着厚厚的、两边已经翻烂了的两本侠义小说。在顶棚上和被烟熏黑了的墙壁上还挂满了小手锯、钻子和抽楦子用的钳子等家具。但是,这些家具上面已经结满了蜘蛛网。麦提亚孜有铁匠、木匠、鞋匠和理发匠的手艺。
他当鞋匠时,靴子的楦子、裁刀、小锤子、锥子、针都是自造的,当理发匠的时候,从剃刀到掏耳勺等家具也都是自己造的。 他替同村的人缝补皮鞋,修理铁盒铁缸子,修理套具。从来不计较工钱,就是什么也不给他,只说声“谢谢你”,他也会心甘情愿。若是送他一两碗奶皮茶喝,那他就会高兴得像上了 。虽然如此,但是,很多人却都不愿意找麦提亚孜修理自己的东西。
因为麦提亚孜的本行原是理发匠,这个手艺是他父亲传授给他的,并且在父亲的督促下干了十几年,每当他稍微有些懈怠的时候,他父亲就会马上拧一拧他的耳朵。父亲去世后,他便改了行,把理发店改成售卖葵瓜子和大豆的小摊子。没过多久,摊子荒了。后来,到了春天,麦提亚孜自己糊了些风筝重新又把这个摊子架起来。但是由于生意太小,交不起房租结果,这间铺子也被房东收回去了。
从此以后,他便搬到几年前他父亲给他遗留下的那间带花园的小屋里来住。由于麦提亚孜对每件事都细心留神,他的其他手艺都是看着农民的需要自己在那里摸索学成的。不过,他做事总是有始无终。或者是断断续续,每一件事总要顾主不急不慌而有耐心地等待才能做成功,有一个农民曾经叫麦提亚孜修理一个车轮子,他往麦提亚孜家跑了六个多月,也骂了他几次,可麦提亚孜仍然拿一副嬉皮笑脸来回答他,这么一来,当然也就跟他吵不起来了。 无论怎样,因那农民催促得紧,那付车轮总算是修好了。
麦提亚孜有些时候也给农民们剃剃头,修修胡子。要叫他剃头么,最好是没什么急事,而且要有耐心才行。他先让剃头的人蹲在门前大石板上,再把那个人的头干搓个十五分钟,然后在手心里捧着水从指缝里淋下去,又开始湿搓。这样的动作延续很久,洗头的脏水顺着那个人的耳根、眉头流下来,弄湿了他的衬衣,但是,这位剃头匠却满不在乎,还一边讲着旧小说里的故事给别人听,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忘记在给人剃头。直到蹴在石板上的那个人提醒他说:“匠人,头发干了”,他才一边又开始用水润发搓头,一边还滔滔不绝地继续说着他的小说章回: “那吉姆西特王把所有的东西都输给赖丽瓦西之后,又把他漂亮的妃子——德丽素紫公主也押了赌,结果赖丽瓦西把这个美丽得像仙女般的公主也赢走了,嘿!嘿!嘿……”他对自己所说的故事也自鸣得意地笑起来了。
可是,在别人看来,却很难分辨出他是哭是笑。当他笑的时候,他那两只椭圆形的眼睛眯缝得几乎看不见了。他那卷进嘴里的稀而黄色的一小撮胡子便向上翘起来。他的头经常稍向胸前垂着,他是一个忠厚而又幽默的人。所以别人都不讨厌他。
但是有时看到他那惹人讨嫌的样子,又忍不住要嘲弄他几句。 土改的那年,干部们把这个村子里的一个恶霸地主的五百五十亩地分给了这儿的贫农。其中麦提亚孜分到了约撒七八恰拉种籽的一块上等地。一九五三年,他已经四十岁了,才在这块土地上生平第一次干起了庄稼活。虽然说麦提亚孜种了地了,但是他到底自己没敢下手犁地。
在一个天晴日暖、春风拂面的早晨,麦提亚孜背搭着双手踱来踱去地欣赏着广阔的田野。太阳把越来越强烈的光和热慷慨地撒在大地上,蒸发着的田野扑鼻撒来润土的香味,整个冬天睡眠着的虫类,开始蠕蠕地走出它们的洞穴;到热带去过冬的候鸟也已经回来了,正在忙着建窝建巢。农民们匆匆忙忙地准备着春耕。这天,我们的新农民——麦提亚孜也站在田塍上正在考虑着“如何处置这块地?”他却没有发觉已经走到了他跟前的艾木拉。 “嗯,匠人哥,您打算怎么处置这块地呀!”艾木拉微笑着问道。
“我想在它当中修个花园,周围垒起高山,你看怎么样,艾木拉江?”麦提亚孜开玩笑地说。 “这么说,你是想把你花园里盛不下的那些野草闲花都要移到这个花园里来罗!” “俗话说:‘石灰匠当了蜂蜜匠,眼睛里会沾满眼屎。’轮到我们头上的事,当然只有这样。” 麦提亚孜常常在人们面前就这样宣扬自己的疲踏散漫劲儿。因此他常对别人说:“当我上鞋底的时候,锥子往往钻在鞋底下睡觉呢。
” 艾木拉倒喜欢麦提亚孜的这种爽朗豁达的性格,但也常常批评他的一些不合情理的事儿,鼓励他做事放利索一点。 “老鼠屎快凉了,快放到嘴里去吧。”艾木拉目示着在麦提亚孜手心里放了好一会没往嘴唇里放的纳司烟说。 “你也很明白,胆虚是鬼干的事。”麦提亚孜把纳司烟放到嘴唇里,再用舌头往下压了压,把没压进去的两三粒纳司烟喷了出去,怪声怪调地继续说道: “这块地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如果有个买主,恨不得干脆就把它卖掉,好好地吃些油水。
” 艾木拉被烈日曝晒得焦红的脸立刻呈现了紧张的表情,他紧蹙着横卧在羊眼上的两道浓眉说道: “共产党把地分给农民不是叫他们做买卖的,是叫他们生产的。” “是,是这样。” “嗯!既然是这样,你就应该在这块地上种些庄稼,等收割了以后,你吃它也好,换来油水也好,那就随你的便了。” “我看犯不着买来买去的,不如干脆就把这些个油菜籽种到这块地上,岂不更好。”麦提亚孜放开嗓子笑起来。
艾木拉原先只当他开玩笑呢,后来,从他的这个玩笑中竟意味到了他想要在这块地上种油菜,便高兴得笑起来了。 “好吧!匠人哥,就在这块地上种油菜吧!”艾木拉把生铁般沉重的手掌往麦提亚孜的肩上一拍,继续说:“我帮你耕地撒种籽,你找一缸子菜籽就行了。” 就从这一回以后,麦提亚孜在艾木拉的倡导下开始种地了。艾木拉地帮着他犁了七八恰拉多地,又帮他撒了那块地上的菜籽。为了报酬他,麦提亚孜自动地许诺给他缝双皮鞋。
麦提亚孜给一家富家修好了一个马鞍子,赚了十哈达包谷。他就在另一块地上撒下了一恰拉包谷籽,包谷没长出来,但他的油菜倒长得挺丰茂,橙黄色的油菜花,散发着它独有的馥郁。剩下的一普特地,他一会儿想种瓜,一会儿又想种洋芋。结果,就这样三心二意的,什么都没种成,白白把地荒芜了。麦提亚孜在种了地以后所干的活:整个一个夏天就只浇了三次油菜地,这活也轻轻松松地混过去了,因为,他所有的地都挖了两个浇口,油菜地只要一个浇口就浇足了,也用不着干塔坝堵水的活。
麦提亚孜最怕的是夜间浇水,因此,这三次水都是在白天浇的。但是当他浇第一次水的时候,水没顺从他,溢到大路上向别人的地里跑去了,给人家添了许多麻烦。就在那一天,他在水里、泥潭里栽了好几个筋斗,衣服上沾满了污水和泥巴,他觉得不好意思见人,便偷偷地跑回家去了。如果说麦提亚孜怕在夜间浇水,那么今天白天在收割油菜的时候,他又怕热,仰面躺在桑树下幻想着:“桑葚成熟啦,落到我的嘴里来吧!” 他慢慢地抬起了头看着那遥远的田野,只见互助组的丰硕的小麦垂着穗头,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田野的一角,又隐隐约约地看见一群人在不停地蠕动。
这些人都是互助组的组员们,他们就在昨天晚上开会讨论了收割的问题,今天天刚发亮,他们便一齐出动了,大伙儿在割着小麦,麦提亚孜索性把充满忧郁的眼光从互助组的那一个方向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巡视着那些长得亭亭玉立的、碧绿阔叶的包谷;巡视着瓜地上的绿荫棚;堆积在沟边的草堆……。这时,沿着沟边的羊肠小道走来了几个农妇,他们有的手里拿着缸子,有的肩头搭着搭裢,有的还背着大吊葫芦。不言而喻,她们都是互助组的妇女,这是给互助组员们送奶皮茶、馕饼,或者是昨晚就凉好了的冷茶来的。麦提亚孜一眼认出了走在最前头的那个穿着红裙衫的女人,她把花头巾扎在额前,耳朵上还不知夹着一朵什么花呢。她还向周围的那几个女人开玩笑,惹得她们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走来。
麦提亚孜曾经吃过几次艾木拉的妹妹伊扎提汗这个开朗乐观的女人亲手做的美味的饭菜,也曾喝过她亲手沏成的奶皮茶。要是现在她把那正提着的吊葫芦里的冷茶给他倒上一碗,那该多好呀!尽管麦提亚孜垂涎地看着吊葫芦,但是,他那自尊心却不敢让他把伊扎提汗叫过来。他只是用力地咽下了哽塞在喉咙里的唾液,又把头枕在原处开始回想着伊扎提汗:伊扎提汗长得多么健美啊!她像她的哥哥艾木拉那样慈爱地对穷人。他心里想:“胡大为什么舍不得把这样的女人给我呢?”麦提亚孜追忆着伊扎提汗的那副长得像他哥哥一样浓黑而弯曲的眉毛;那两只长着长长的睫毛的羊眼睛;石榴一般的双颊和那健美的身材。他又想起了他在春天用细麻绳量她的脚样的时候,她那胖嫩嫩的大腿碰触了一下他的手腕,使他立刻感到浑身烧灼。
这以后当他偶然看到伊扎提汗挂在绳子上曝晒的裙衫,也会使他神魂飘缈。甚至于他正在缝着的伊扎提汗的那双皮鞋,尽管还没有穿到她的脚上,他也觉得在他家里再没有比这个更亲热更可爱的东西了。他不时地把它放在手掌上抚摸着说:“呀!这双鞋不就是她穿的吗!”用伊宁皮革缝制的这双皮鞋,四月间就绱好了鞋帮子,五月里才绱完了鞋底,上了楦子,现在只剩下擦油上色,抽楦子了。可是他感到直到今天还没有把皮鞋送去而羞愧起来了。他爬起来坐在那里,很久很久地凝视着女人们走去的方向。
二 麦提亚孜放下了收割油菜,便给伊扎提汗的皮鞋上色擦油。他给她送这双皮鞋以前,把皮鞋拿在手上瞪视了好一阵,看,这双皮鞋擦得多么光亮啊!他用袖子又把鞋头擦了擦,然后就把它裹在黑花手帕里了。手帕发着汗臭味,皮鞋发着黄蜡味。 傍晚,正当艾木拉全家聚坐在葫芦藤叶搭起的绿荫棚下吃晚饭的时候,麦提亚孜提着皮鞋进来了。他刚踏进院门,一股拌着香菜的汤面条的香味迎鼻扑来。
艾木拉高兴地迎接他: “好啊!快请,快请,请上坐,匠人哥。”给他指着炕桌的上座说。“嗨!你的马几乎迟到一步。” “不用,不用,谢谢你,我就回去。我是送这个来的。
”麦提亚孜一边说着一边把皮鞋递过去。 伊扎提汗微笑着走过来把皮鞋接过去了。艾木拉强拉着麦提亚孜坐在桌子旁边说道: “今天太阳打哪头出来的?匠人哥。” “哟!我真以为这双皮鞋要到沙漠上开了花,骆驼尾巴触了地才给我做成呢。”伊扎提汗也开起玩笑来了,麦提亚孜虽然平时也很会开玩笑,但是处在现在的这种场合下,尤其是当着伊扎提汗的面觉得很是窘迫尴尬。
因此他一声也没吭,红涨着脸在吃饭。周围的人把皮鞋接过去巡视了一遍,并且连声夸赞它,突然,伊扎提汗的小儿子艾尔肯抢着一只鞋子跑了,他妈一追他,他便扑到麦提亚孜的怀里去了。 “这是你给我送来的,啊?!” “嗯!” “这双皮鞋给我穿,啊!麦亚伯伯。” “给你妈妈吧,我再给你买一双又漂亮又红的皮鞋好吗?” “给我吧,我的宝贝,给我拿回去。” “嗯!等着吧!” 当伊扎提汗从她儿子的手里夺取皮鞋的时候,她那又热又柔软的皮肤碰触到麦提亚孜的脸上了,麦提亚孜尽力地抑制着他几乎像水银一般熔化了的身体,但是,他还希望这个景象多延续一会儿,可惜伊扎提汗把皮鞋从小孩子的手里夺过去就走进屋里去了。
麦提亚孜便开始酣闻那孩子被妈妈的馥郁浓香渗透了的脸颊和耳根。 这个孩子当他刚生下六个月的时候,就死去了爸爸,他妈妈就把他带到艾木拉家里来了。因此,他是渴念着父爱和温暖而长大的。伊扎提汗呢,自丈夫去世以后,整整守了四年寡,因为她苦苦的怀念着那去世的丈夫,所以,就再也没起改嫁的念头。虽然曾经有人跟她谈过亲事,可是,在这些对象中,有的爱吵架,她怕受折腾,有的有孩子,她又怕欺侮了她的孤儿,所以就一一都推却了。
那么对麦提亚孜呢,却根本再无须乎考虑这些个事情,但是伊扎提汗又讨厌他的疲踏劲儿,只要他能像别人一样快手快脚地劳动,那么伊扎提汗当然愿意跟他同家共居。 艾木拉把吃过饭的碗盘叠起来往一边推了一下,就和麦提亚孜聊起割油菜的事情来了: “匠人哥,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把油菜撇下了?” “我看,割田也像学手艺一样,我还没学会这个手艺呢。” 艾木拉早就知道麦提亚孜想用“手艺”来掩饰他自己的懒惰,冷笑着瞟了他一眼: “你这个人,乍一看便像个直爽人,细细一看却像个刁滑的人,你干脆就说:‘我怕太阳晒’,把真心话说出来不就得了么?” “你说的倒是真话。”麦提亚孜觉得艾木拉的话锋正击中了他的要害,感到羞愧,接着说道:“但是……不过……究竟怎么割法,我还没有摸到门路,你瞧瞧——”说着便把被镰刀割出了几道伤痕的手伸给艾木拉看。 艾木拉连看也没看一眼,带着讽刺的口吻说道: “当然,割田也得学会它,只要不怕太阳晒,不怕劳苦,不到两天就学得会,但是这活路却不是你那高兴做就做,不高兴做就撇下的破烂鞋。
现在,一天的松懈,就会糟蹋几个月来的劳苦成果的。” “对,对,你说的对,现在让我怎么办呢?” “我不是在给你说吗?现在不是你东考虑,西思量的时候了,你应该赶快束紧腰带把它收割起来。” “收,当然要收的,说真的,这活已经把我整垮了。” “唉,匠人哥——”艾木拉显出悲悯的神情说。“打场收场并不比收割容易。
这全靠你的耐心啊!” “你说是要有勇气是吗!” “唉,这才说对了,是需要勇气。所以就得清早动身割田,直到太阳辣了,你再到树荫下憩息一会儿也可以,如果你能鼓起勇气的话,月夜下也可以收割。一到晚上油菜茎就潮润了,割起来也容易,而且菜籽也不易撒掉,你自己也不受太阳的晒烤,如果经常这样鼓起勇气来的话,一切事情都能按时做完。” 麦提亚孜满口答应艾木拉给他出的主意,要鼓起勇气来继续收割油菜,他便带着这个决心回家来了,因为他决心明天大清早就要起身,他便放弃了像往常那样每天晚上坐在礼拜寺门前扯闲谈的习惯,今晚比村子的人们睡的特别早些。可是当村子里的人都已经进入梦乡了,他却还没睡着,他一会儿苦思着命运注定跟他为难的那些油菜,一会儿玩味着伊扎提汗刚才挨触他的面颊的引人入神的灼热的皮肤,和她那俊美的容貌。
因为这些连苦带甜的遐想,不让他安息,他便翻来覆去地直到鸡叫头遍才睡着。 麦提亚孜由于睡得酣熟了,所以东方发亮的时候,他还没有醒来,当太阳的鲜红的光芒照亮了他的窗户,屋子里的苍蝇开始嗡嗡地骚扰的时候,他才懒洋洋地爬起来,连脸都没洗就开始烧茶了。他知道这时农民们都早已上地了,他懊悔他第一次鼓着勇气像他们一样地去干活的这头一天就迟到了。这位新农民还不习惯于早睡早起,他在平时,每天早晨总要太阳升起来才睁开睡眼。无论怎样,他今天比往常起的是早一些,这也是值得我们庆幸的事情。
你瞧,他也正在着急呢!为了燃着火,不断地用嘴吹着火,两眼被烟熏得直淌眼泪。 “愿上帝永远不叫你燃着吧!”他一边朝着吹不着的灶火嘟哝,一边擦着眼泪。后来他索性不想喝茶了,就用他那条包过伊扎提汗的皮鞋的手帕,包了一块干硬的馕,夹在胁下,拿了一把镰刀走向田地里去了。一路来,他的鞋子不断地拍打着他的脚踵,他的鞋子,也似乎感到主人今天的步伐和动作比以前快了一些而为他高兴;啪,啪,啪地直响,好像在为他拍手欢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