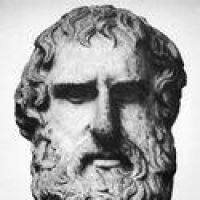普拉斯
/其他
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是继艾米莉狄金森和伊丽莎白毕肖普之后最重要的美国女诗人。1963年她最后一次自杀成功时,年仅31岁。这位颇受争议的女诗人因其富于激情和创造力的重要诗篇留名于世,又因其与另一位英国诗人休斯情感变故自杀的戏剧化人生而成为英美文学界一个长久的话题。

简介:
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0.27 - 1963.02.11)
西尔维娅普拉斯(为我们所熟悉,首先是作为一位美国自白派诗人的代表,上世纪80年代就被介绍进来,并对国内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生平:
普拉斯出生于美国麻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地区,她8岁时父亲去世,她和弟弟由母亲抚养大。1955年,普拉斯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著名的史密斯女子学院,之后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在那里,她遇到了后来成为桂冠诗人的特德休斯(19301998),两人于1956年6月结为连理。在与休斯育有一子一女后,两人婚姻出现裂痕并于1962年9月分居,普拉斯独自抚养两个孩子。1963年2月11日,她在伦敦的寓所自杀。
著作:
生前,普拉斯只出版过两本著作,一是诗集《巨人及其他诗歌》(The Colossus and Other Poems),另外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钟形罩》(the Bell Jar,中文译本今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电子版由译言古登堡计划于2013年12月26日出版)。去世后,特德休斯编选了几部普拉斯几本诗集,奠定了普拉斯作为一名重要诗人的地位,包括诗集《爱丽尔》(Ariel)、《渡湖》(Crossing Waters),《冬树》(Winter Trees)及《普拉斯诗全集》,后者于1982年获得普利策奖 。本小辑选译的作品来自1977年出版,由休斯编辑的《约翰尼派尼克与梦经》(Johnny Panic and the Bible of Dreams),这是一部短篇小说、散文、笔记的合集。
普拉斯的小说创作有非常突出的自传性特色,几乎每一篇都能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中找到影子。作为诗人的普拉斯也曾非常投入地学习过绘画,这些特点都鲜明地体现在本小辑所选的这几个短篇中:感情细致入微,用词不俗而且准确,描摹景物富于色彩感,因此赋予她的小说一种独特的阅读快感。《绿石头》是对童年生活令人怅惘的追忆;《超人与宝拉布朗的新冬装》叙述的是成长经历;《寡妇曼加达其人》根据作者新婚后去西班牙度假的经历写成,体现了过人的观察能力;《成功之日》记录了一对献身写作的夫妇的生活及妻子微妙的心理活动,联想到普拉斯本人,读来令人感慨。
她的部分著名诗歌有: 十一月的信;雾中羊;邮差;榆树 作为悔悟的幻想之光;语言;爱丽尔;边缘;晨歌;穿黑衣的人;词语;冬天的树;渡湖;对手;巨像;慕尼黑女模特;你是;十月里罂粟花;等等。
气质:
艺术家总是一些异类,他们身上有一种神秘的特质,从远处看,绚丽夺目,缤纷斑斓,造成了他们作品非同凡响的品质。但赋予他们作品奇异的精神元素同时也影响着他们精神的歧义。艺术家是天生的。因为,在他们精神中有一种普通人不具备的素质(我选择怎样的字眼好呢):疯狂、迷幻、极度的忧郁或痛苦、不能控制的激情、专注于自我、幽闭或狂躁等等。翻开一部艺术史,令人伤心地看到,那些一流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感到自己处在一种精神崩溃的边缘;有的则直接走向精神崩溃的深渊。精神分析家们从中可以找到丰富的个案进行研究,并毫无困难地宣称,心理的异常正是造成他们作品非凡的根源。可是,令人喟叹的是,这一点并不由你选择是要生活正常,还是要艺术上的非凡?
凋零:
伦敦。1963年2月11日的冬天,异常寒冷。西尔维娅躲在一间小屋内,孩子们在哭泣,壁炉内是潮湿的,窗外下着雪,诗稿凌乱地撒在桌上、地上,她头发飘闪,神情紧张这是我想像中的《西尔维娅》电影的一个场景。那一年,她年仅三十一岁。生命的花朵正是艳丽开放的时刻,却突然凋零了。一如乌云洒下一面镜子去映照自己缓缓/消逝于风的摆布。她在诗歌中曾经这样暗示着。死亡,更确切地说,是自杀,在她的心灵深处被美化成一次优雅的舞蹈,一种自我的飘扬,是雪花般圣洁绽放后的迅速融化。
成长历程:
童年
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 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美国著名的自白派女诗人,小说家。她的父母均为教师,八岁那年她父亲去世。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到死亡,也是她一生的转折点。当母亲告诉她父亲的死讯时,她决然地说:我不再与上帝通话了。之后,她不断在诗中歌吟死亡,也曾多次试图自杀:
死去是一种艺术/和其他事情一样/我尤善此道。我又做了一次/每十年当中/我要安排此事。看,黑暗从爆裂中渗出/我不能容纳这些,我容不了我的生命。从灰烬中/我披着红发升起/像呼吸空气般地吞噬男人,像猫一样可死九次。这女子已臻于完美/她死去的/身体带着成就的微笑。
大学
在大学期间她学业出众,每门功课都是优等,获得多项奖学金。大学二年级时因出色的写作才能被纽约时装杂志《小姐》选中应邀担任该杂志的客座编辑。一个月的纽约生活如同梦幻一般,豪华的宴会,漂亮的时装,与仰慕的作家共同创作。但好景不长,不久她就陷入在精神分裂的磨难中,直至进入麦克林精神病院被进行电疗。她的自传体小说《钟形罩》(The Bell Jar)就是描写这一段经历。
这部小说如同她的诗一样,是她的精神自传。在小说中很少有明晰的场景,主要是她通过自我之眼看到的变动的、片段似的、梦幻与现实交织在一起的景象,犹如她内心独白中闪回的布景。小说被丰盈的自我感受所包围:青春期的烦恼、热烈而莫名的向往、跃跃欲试的冲动、期望被男人勾引、对未来躁动不安的憧憬和犹疑不定的选择,企图尝试一切又逃避一切的心理、疯狂地冒险和极力地压抑一如用快速的镜头扫过内心所有的角落,一个矛盾集合的多元体,像是在玻璃杯中倒入令人迷醉的幻象并用现实加以搅拌。她一边用变换的场景来作她心情的告白,一边用严格的句子写下头脑中混乱的思想。真是一部杰作!
她的极度敏感形成了她容易受挫的心理;迷恋内心生活使她易于与现实进行对抗;过分好强造成她疲惫和虚弱;对事物完美的追随促使她对自己过多的抱怨;精神压抑其实是来自心灵的亢奋;对生命的认真推动她最终走入生命的虚无;追求诗歌的深度却在心中布满了痛楚。所有这一切又可以反过来认证。原因和结果在她的心内是同为一体。晕眩与纯净,错觉与清晰,恐惧与喜悦,黑暗与宁静,愤怒与怜悯,亲切与卑微,死亡与新生就是这样交织在她的诗中,也成为《钟形罩》的意象源泉和氛围元素,宛如雨滴淋湿了书中的标点。
英国留学
西尔维娅普拉斯和特德休斯 1956年2月,西尔维娅普拉斯获得一笔奖学金获准去英国剑桥留学。她在那里邂逅了英俊的英国诗人特德休斯(Ted Hughes,1930 1998),两人立刻坠入了情网,并闪电似地结婚。当时普拉斯称休斯为世间惟一能与我匹配的男子。但不幸的是他们的婚姻出现了裂痕。有人怪罪于休斯的风流;可能更隐蔽的原因是出于普拉斯难以控制的疯狂。1962年普拉斯与休斯分居,她单独带着儿女在伦敦居住。同年休斯与Assia Wsvill同居。普拉斯在数月内突然面临的剧烈的生活变动,以及生活拮据所带来的压力,《钟形罩》刚刚出版却反映平平,与休斯办理离婚手续过程中承受的巨大的精神痛苦,促使她再一次地选择了自杀。但这一次,上帝成全了她。从她到英国至死亡正好整整六年。
在世人眼里是这场婚姻造成了她自杀的导火线。休斯成了不可逃避的罪人。她的小说和诗歌也由此获得了好评。直到她死后二十多年,休斯才出版了他的诗集《生日信札》(Birthday Letters),这是写给普拉斯的诗。诗集出版立刻引起了关注并唤起了人们再度对普拉斯的热情,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世人心目中休斯是罪人的看法。据此,英国和美国为纪念普拉斯逝世四十周年刚刚拍摄完她的传记影片。
奖杯
普拉斯的杰出成就是不可模仿的,她用一种精神直觉来直接抵达作品的深处,她挖掘丰富的自我和情感因素,用全部的生命力量进行创作,直至内心出现幻象。说不清是因为疯狂形成了非凡的作品,还是由于这样的创作方式造成了他们的疯狂。自白派中另一位诗人洛威尔也步普拉斯的后尘进入了麦克林精神病院。大提琴家杜普雷因癫狂而崩溃。吴尔芙最终难以抵御内心的忧郁在口袋中装满鹅卵石走入河中他们都是过于敏感的人,时常不能摆脱内心幻象,是以精神直觉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唉,生命是一曲赞歌也是一曲挽歌,正如普拉斯在《钟形罩》中所说:奖杯上刻着的日期就像墓碑上的日期一样。
他人评议:
普拉斯诗歌中死亡主题探究--作者/刘 燕,陈 蕾
一、女性主义和普拉斯概述
女性主义是20世纪广泛兴起的在政治、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反抗男权、争取女性自由的运动。长期受压抑的状态使广大女性在这场运动中奋力寻找自己的声音和身份,逐渐改变性别弱势的状况。这一运动的兴起,相伴着女性文学的兴起和繁盛。一大批文学巨擘先后涌现,一方面波伏娃,弗里丹等文学理论家已在文学史册上永绽光辉,另一方面,大量的女性作家和她们的文学作品也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理解甚至改变女性的生存状态。
普拉斯的诗属自白诗一列,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一种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当普拉斯于1960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巨像及其他》时,读者和评论界反响并非十分热烈。到了1965年即她自杀后的第三年出版的诗集《爱丽尔》才开始为她赢得声誉。尔后由其丈夫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整理并出版了她的两卷诗集《渡湖》和《冬天的树》,把普拉斯作为自白派诗人的声誉推向了最高点。至今,她依旧声名不衰,尤其是1998年休斯的遗作《生日贺信》又再次勾起了人们对普拉斯深深的怀念之情。她的诗艺与人生悲剧无法分开。普拉斯不仅成为后现代主义自白派的代表,而且也因其作为女性作家为创作所做的努力和其诗歌中对男权社会的反叛精神成为女性主义文学的碑石。
二、死亡作为抗争
西尔维娅普拉斯在诗歌形式上继承了惠特曼的传统:简洁、大方、自由,没有雕琢的痕迹,好像是自然流淌出来的,但内容上别开生面,很少顾忌,残缺的肢体、肮脏的角落、恐怖的病房,都能借来人诗,又因为诗人是女性,其视角就更为独特,所选择的意象更为敏锐。尤其是普拉斯与丈夫分手后,内心一片茫然,光明不复存在,写出的诗越发刻薄,也越发深刻。
在普拉斯一生的诸多恶梦中,父亲像一座巨大的雕像投下了沉重的阴影,使她一生都为之负罪累累,痛苦不堪。普拉斯为逃避孤独曾经将父亲当作自己的偶像,但后来这个偶像反而变成了对她个人生活最大的威胁,全部人生信念从此崩溃。女性主义认为父权为中心的社会机制是女性受压抑的根源,因此,抗争父权或男权成为其不懈的动力和目标。在众多女性作家笔下,寻回话语权,找回女性意识,重置迷失的身份都是抗争的手段。普拉斯在其狂暴内心的指引下,描述了大量以死亡为意象的诗歌。虽然一方面评论家们一致将她个人的生活经历作为解释她笔下黑色艺术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女诗人从其女性角度出发对父权社会作出的反抗。
《爹爹》这首诗歌充斥着浓重的压抑气氛,她写到:你是只黑皮鞋/我曾像只脚住在这里三十年/穷困和悲凄/只敢呼吸和抽泣。诗人将她的父亲比作法西斯、魔鬼等,而诗人自己却以犹太人自喻,深刻的揭示了其成长环境的压抑状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人类进入父权社会后,女性在社会、家庭关系里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在性别权势中低于男性,长期受到男权社会的束缚。在普拉斯的诗作中,这类受压制、受束缚的状态透过其女性的独特体验,如分娩,对身份的转变感到惶恐不安,对新生儿的亲近与排斥,对父亲的复杂感情,对丈夫的爱恨交织等等。
然而,在诗中除了凝重的压抑感,读者仍能体味到诗人对父亲的爱和依恋。普拉斯将父亲比做法西斯,但却写到,每个女人都崇拜法西斯分子,那人(指其父),把我可爱的红心一咬两半//我十岁时他们埋葬了你//二十岁时我有死的意图/回到,回到,回到你的身边,哪怕你已变成白骨。诗人甚至将自己和她父亲合为一体,要是我杀一个人,就等于杀两个人,从这些诗句中,普拉斯对其父亲的依恋清晰可辨。结合到诗人的经历,评论家也认为这种对父亲的复杂情感也是她对背叛自己的丈夫的感情写照。
正是这种爱恨交加、依赖和埋怨相间的感情,使女诗人在精神上愈加痛苦,受尽煎熬,最终进发了那撕心裂肺的呼喊,爸爸,我要杀死你,/我来不及动手你就死去/一尊可怖的雕像大理石般沉重。诗中她还把父亲比作魔鬼、法西斯、希特勒,流露着嘲讽、反感、怜悯的复杂情感。在《爹爹》这首诗里,除了表现某种希望的破灭外,它也许不能单纯理解为字面意义上的父亲,而抽象延伸为一种象征失望、异化、邪恶、神秘、怨恨以及男女性别对立等诸种含义。普拉斯在这首诗里,一连也用了好几个黑字,你站在黑板前面,你是只黑皮鞋/一身黑的男人,/那架黑色的电话机被连根拔起/你那肥厚的黑色心脏里有一根标桩/因而村民不喜欢你。这几个黑字固然与她惯用的以黑色作为艺术底色有关,在看到普拉斯对希望破灭后的绝望和难以排遣的郁恨中,也让人看到了她对崇高和阳刚之美的彻底否定。
最终,诗人以死的志愿结束了这种精神的折磨。爹爹,爹爹,你这混蛋,我结束。从中可以看出诗人以死相抗,来显明自己抗争压抑、抗争父权的努力。
三、死亡作为妥协
普拉斯的诗显而易见具有某种类似于疯癫状态的狂躁气质,它们不仅有许许多多突兀的、出人意料而又光芒四射的意象和意味,难以穷尽的象征、隐喻,而且诗的语言也往往打破逻辑和时空的顺序、而随意识自由地驰骋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成为超越理性束缚和心理屏障的精神载体。她的意识在摆脱理性的限制而濒于疯狂之际,往往能直接洞穿生命的内核,论言妄语成为最灿烂夺目的诗章,就像在《女拿撒勒》中体现的那样,天才与疯狂悲剧性地统一在一起,令人惊叹又惋惜。
相较于《爹爹》,《女拿撒勒》这首诗以更加直白的方式讨论死亡。死,是一种艺术,象一切其他的东西。从该诗的最后一节来看,我披着一头红发/从灰烬中升起,/象呼吸空气一样吃人,该诗表达的是强烈的反抗意识。在经受了男权的压抑,诗人渴望通过死亡来摆脱这种痛苦,并进行最强烈的反抗象呼吸空气一样吃人。
当结合到诗人之前的叙述,诗人的渴望只能是其终极的幻想。首先呈现于读者眼前的是诗人对死亡的眷恋,我又尝试了一次,/我十年/尝试一次,从中读出的是诗人曾经的自杀企图。接着我是一个笑容可掬的女人,/我仅仅三十岁,/我象猫一样有九条性命,//这是第三条/每十年就要消灭/一个废物!此处进一步验证了诗人对生之厌恶。之后,普拉斯再一次提及之前的自杀经历。第一次发生在十岁,那是一次意外,/第二次是我有意,要干出个明堂,/根本不愿回头。
在诗歌中,死亡的意象也比比皆是,纳粹的灯罩、镇纸上等犹太人亚麻布、那条餐巾等等。然而从这几句我这样干使自己感到死是地狱/我这样干使自己感到真死,/我猜想你们会说我身负某种使命,感到诗人隐隐地为着某种力量所折服。死亡是恐怖和真实的诗人自己明了,可她仍揣测着世人知道其死后的猜想,这似乎带给她某种满足感身负某种使命。仔细阅读诗歌,这种使诗人折服的力量来自诗中所指的我的敌人,敌人先生。我的敌人使诗人放弃生之希望,奔赴某种使命。
结合到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为了摆脱对父亲的爱恨交加的感情,普拉斯曾有过几次自杀尝试。在丈夫背叛她另结新欢后,普拉斯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自杀,并最终离开人世。诗人试图摆脱父权的压抑,妄图以死相抗,可是最终成为一种向敌人先生妥协的方式?我的敌人强化了男女两性的对立,也让人们看到了诗人的妥协。
四、死亡的终结,不尽的猜想
普拉斯的诗歌穿梭于自白、自我、自杀之间,并将罗伯特洛威尔所开创的一代诗风推到了顶点,实现了WB叶芝所谓的20世纪诗歌将是心灵发出的叫喊的夙愿。她是一个内心狂暴的诗人,她在用生命写诗,也在用死亡锻造黑色艺术。某种意义上说,她要通过诗的形式控告男性作为整体,在婚姻、家庭、社会上给女性造成的伤害。按照普拉斯的理解,女性因男性的压迫心理逐渐扭曲,原本完整的人格变得支离破碎。
通过《爹爹》、《女拿撒勒》两首诗歌中死亡主题的探究,普拉斯以死亡为武器来对抗男权社会,还是以死亡向男权社会妥协,都尽得剖析。最终诗人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也让人们不断地揣测诗人的死是抗争抑或妥协。
- 七年级英语下册 上海牛津版 Unit3
- 沪教版牛津小学英语(深圳用) 四年级下册 Unit 2
- 沪教版八年级下次数学练习册21.4(2)无理方程P19
- 外研版八年级英语下学期 Module3
- 二年级下册数学第三课 搭一搭⚖⚖
- 沪教版牛津小学英语(深圳用)五年级下册 Unit 1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老山界》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安徽省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泊秦淮》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辽宁省
- 8.对剪花样_第一课时(二等奖)(冀美版二年级上册)_T515402
- 三年级英语单词记忆下册(沪教版)第一二单元复习
- 沪教版牛津小学英语(深圳用) 四年级下册 Unit 7
- 人教版历史八年级下册第一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精品·同步课程 历史 八年级 上册 第15集 近代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
- 北师大版八年级物理下册 第六章 常见的光学仪器(二)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 19 爱护鸟类_第一课时(二等奖)(桂美版二年级下册)_T3763925
- 外研版英语三起6年级下册(14版)Module3 Unit1
- 沪教版牛津小学英语(深圳用) 五年级下册 Unit 10
- 苏教版二年级下册数学《认识东、南、西、北》
- 冀教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第二单元《有余数除法的整理与复习》
- 沪教版八年级下册数学练习册一次函数复习题B组(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