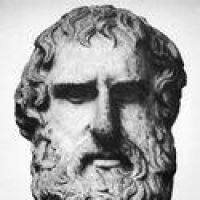周波
/文学
澳门也是我的第二故乡
作者:周 波
“昨晚上,我又梦到荷兰园,梦到你奶奶了!” 父亲抽着烟,斜倚在沙发上,随意地、絮絮地说着,表情随一缕烟气迷离起来。父亲一向是个活得风风火火的人,少见他这种语气和神情,我悄悄地又看了他一眼。透进窗棂的天光正落在他稀疏的头发上,朦胧的灿烂,就像故事要开场,听的人围了一圈,一双双炯炯的目光在黑暗中发亮,都盯着台上的那人。唯一的灯射着,不知怎的,像初期的黑白电影,粗糙的幕布上有断断续续的黑线雨似的下。无论如何,旧事都到眼前——荷兰园是父亲度过童年时代的一个地方,在澳门。
相较其他70年代在内地土生土长的普通女子来说,我知道澳门恐怕算早的。那是在我七岁的时候。 我的童年并不愉快。因为“爬格子”的父亲是“右派”,我和弟弟在小朋友中间不太被瞧得起,常常是对垒的“两军”,哪方面都不要我们加入,甚至中弹“牺牲”这种谁都不愿扮的角色也轮不到我们演,还常常被人追在屁股后头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会打洞!”那般脆生生的响彻天地间的童声直叫得天也厚了、低了;人也远了、小了,至今还会在耳旁隐约响起。 七岁那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本想趁着大人们午睡偷溜出门疯玩一通的我又一次遭了小朋友们的冷落,灰溜溜、偃旗息鼓地回到家里,百无聊赖地趴在窗口看着窗外绿匝匝的结满像苍蝇似的籽的老树,身后是睡在竹床上打着呼噜的父亲。
忽然,父亲说起梦话。我蹑手蹑脚走到父亲头边,努力想听他说些什么,可是,只听到一片“哑哑该该”的,根本就是我不曾听过的语言。 “爸爸!”“爸爸!”好奇的我不管不顾地使劲把父亲摇醒,问他做什么梦,怎么他说的话我一点不懂?我还鹦鹉学舌地蹦了几个字。父亲睡得迷迷糊糊,随口答道,“那是广东话。” “广东话?你在哪里学的广东话,也教我说好不好?” “没有语言环境,教也难教,学也难学呀。
”父亲彻底醒了。 “那你怎么学会的?” “我小时候就会的嘛。” “给我讲你小时候的故事!”我赖到父亲身上。 父亲总是奈我不何,说道:“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叫荷兰园——” “荷兰园也是学校吗?”我又插嘴。 “不是,”父亲笑盈盈地说起来:“荷兰园是一个很漂亮的住宅区,在一个叫澳门的地方,那时候国内到处在打仗,日本鬼子还没打到澳门,汇兑也通,爷爷就让奶奶带着我和你叔叔到澳门避难……” 回忆让父亲年轻但长期眉头紧锁的脸焕发出奕奕光彩,从他绘声绘色的讲述中,我知道:澳门有座大三巴牌坊,是他和伙伴们最常去的游玩场所,大三巴牌坊上有一只鹰;澳门有好多赌场,生下来就有十二斤的叔叔很顽皮,也喜欢“赌”——他是喜“打赌”,一次因为与人打赌,结果掉进凤梨麻堆里,扎了一屁股刺,龇牙咧嘴跑回来,还不敢跟奶奶说,让父亲给他拔刺。
父亲又气又笑,拿把镊子给他拔刺,结果从叔叔的肥屁股上拔出23根刺来,叔叔因此半个月不敢落座;父亲在纪念中学附属小学读书,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抗日游行;因为日本人的封锁,澳门与内地汇兑不通,出生钟鸣鼎食之家,过惯锦衣玉食生活的奶奶租住不起荷兰园的房子,便带着兄弟俩搬到贫民区“聚龙里”,靠她在女子职业学校所学的缝纫技艺过活,端庄、善良、勤俭的她还赢得了周遭穷邻里的尊重,这可不是轻易能得来的;欢庆抗战胜利,澳门街头的爆竹残骸厚达一尺…… 就在我听得兴味正浓的时候,父亲突然戛然而止,一脸正色对我道,“可不能跟别人说爸爸会讲广东话,在澳门生活过,今天我讲的所有东西都不准出去说!如果让人家知道我在想澳门,想以前的生活,爸爸就会被抓起来的。” 一听这话,我立刻把嘴闭紧了,特定氛围下长大的孩子总特别的懂事。但,自此我对这块叫“澳门”的、带给父亲许多童年欢乐的地方充满向往之情;也存疑“澳门”是不是真有扇什么“门”。想象里,澳门有着初冬干寒的空气,一座似中似西的古色古香的塔楼挑高绯色的天,远远的——其实,澳门的气候应该是湿热的。近处,有女子窈窕的背影,穿件玉色织锦缎的夹袄,紧紧小小,有中等人家的温暖、绮丽,她眺望着…… 至于澳门的夜就该是电影《乌鸦与麻雀》、《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场景,细细的、嗲嗲的女人歌声是流动的空气,躲在家中看外面的热闹,灯红酒绿的光扑到窗帘的丝绒上,反射出沉沉的华丽,完全异样的生活,让人心生渴慕。
及至上中学,学到澳门历史,感情上多份亲近,也比旁人多了层遗憾——那被父亲称之为“第二故乡”的土地,我们是不可以随便去的。好在此时政治气候已清明,父亲恢复了文学创作,可以明目张胆地写他魂牵梦绕的“澳门”了。他把他的童年生活写成小说,并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澳门轶事》,他还随着摄制组回了澳门。 感谢科学的昌明,把在想象里反复揣摩、描绘过的澳门用强烈真实的色彩呈现到我们面前:小山环叠,古木参天的白鸽巢公园;有着有趣传说的圣雅各伯小教堂;建于历史悠久的古堡之上的妈阁炮台……我也终于知道大三巴牌坊“长”什么模样了。父亲漫步在澳门的大街小巷,在将现实与记忆一一对应的过程中,生出良多感慨;澳门变了,再不是破破烂烂、衣衫褴褛的小可怜儿,变成风情万种、融会中西美丽的魅力女子了。
而让他感触最深的是,澳门人对祖国的认同感很强,各种传统文化、民族风俗继承得相当好,甚至比内地一些地方做得好。后来,父亲因为公干经常去澳门,有时候还住上一段时间。他常对人津津乐道,说澳门回归前夕他正好在澳门,亲身感受到了澳门人那种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一洗百年奇耻之光荣,游子远别归家之喜悦。 现在给他更多欢愉的是在澳门结识和交往的新老朋友。他觉得澳门人最可贵的是几乎个个温良敦厚,可亲可近,拥有更多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而走在澳门的大街小巷,感受到的仿佛是一种五月的艳阳斜照,坐在临街小馆外的藤圈椅上,有风长长吹起,眯起眼睛时的悠然;一种彼此相觉面善的脉脉温情,繁华却安静——这简直叫人神往了。只有走进赌场,才意识到这里是声色喧嚣、犬马刺激的世界四大赌埠之一。 我很好奇,澳门人是不是个个会赌、爱赌,属于那种即便生病,也只须一剂“麻将煎水”,喝了就好。父亲的回答却让我大大的意外:澳门人绝大多数是不进赌场的,赌场里的工作人员也只有每年大年初一至初三可以赌,其他时间一律不得赌博。太不可思议了!一个被西方殖民者统治了四百多年的地方,为什么它的习俗、理念却更中国、更传统?我问父亲。
父亲沉思了片刻,说,“这恐怕不是一句话说得清楚的!”停了片刻,他又笑言,“将来你自己去寻找答案吧。” 是的,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能到我父亲的第二故乡,亲自去感受、去寻求、去探索…… 突然,从我心底里升腾起一种特别亲切之感——这都因为我的血液当中也渗透了澳门的基因吧。其实,澳门也是我的第二故乡呀!
- 【获奖】科粤版初三九年级化学下册第七章7.3浓稀的表示
- 苏科版数学七年级下册7.2《探索平行线的性质》
- 第8课 对称剪纸_第一课时(二等奖)(沪书画版二年级上册)_T3784187
- 冀教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1
- 8 随形想象_第一课时(二等奖)(沪教版二年级上册)_T3786594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其五)》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辽宁省
- 外研版英语七年级下册module3 unit1第二课时
- 外研版英语三起5年级下册(14版)Module3 Unit2
- 七年级英语下册 上海牛津版 Unit3
- 冀教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第二周第2课时《我们的测量》宝丰街小学庞志荣
- 二年级下册数学第二课
- 北师大版小学数学四年级下册第15课小数乘小数一
- 沪教版牛津小学英语(深圳用) 四年级下册 Unit 7
- 第五单元 民族艺术的瑰宝_16. 形形色色的民族乐器_第一课时(岭南版六年级上册)_T1406126
- 30.3 由不共线三点的坐标确定二次函数_第一课时(市一等奖)(冀教版九年级下册)_T144342
- 冀教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第二单元《有余数除法的竖式计算》
- 外研版英语三起5年级下册(14版)Module3 Unit1
- 冀教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租船问题》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泊秦淮》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辽宁省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老山界》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安徽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