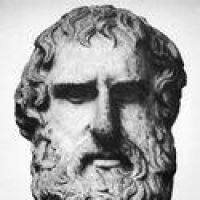杨静龙
/文学
声 音
作者:杨静龙
腊月的一个午后,村口老樟树桠杈上那只哑了大半年的黑漆铁皮喇叭,突然呀地一声唱了起来。 入冬以后,连绵的红土丘陵万木皆黄,被春夏的浓绿覆盖着的丘坡上东一块、西一片裸露出褐红色的土壤。玉水河从丘陵深处缓缓走来,走过坡地和水田,走到了村口,步态轻轻盈盈,像一个大姑娘。 玉水河终于结了冰,冰薄得像学生的一张作业纸。细毛所在的小学校放寒假不久,外出打工的男人们开始一拨一拨地回村。
细毛的阿爸跟着村支书在南边城里建筑工地上承包了一个项目,脸晒得比在田里干活还黑。可姆妈给他脱鞋时,脱出了两鞋底的钱。 夜里,一家人欢欢喜喜围着桌子吃饭。奶奶、阿爸、姆妈、我,还有苍耳,全齐了。奶奶高兴得想唱越剧。
奶奶喝了足足有一斤绍兴黄酒,喝得脸上连皱纹都红亮起来。可她张了几次嘴,终于还是没有唱。奶奶把越剧当成了自己的生命,连说话都像带着唱腔,可她从来没有在人前唱过一句戏。奶奶其实是个只会在心里做事的胆小的人哩。 人上了年岁,就不能高兴太过了。
当晚,奶奶就病倒了。 从山坡上刮过来的风里裹挟着褐红色的沙尘,村口的大樟树枝叶舞动,发出沙啦沙啦的声响。 细毛约了一群伢儿在樟树底下踢石子玩。细毛请伙伴们吃油炸年糕片,油亮焦黄的年糕片放在嘴里,嚼得格嘣格嘣脆响。一脚左,一脚右,三脚四脚前边边跳。
伢儿们踢得兴致足足的,额角上头发让汗粘成了一团抹布。 伢儿们踢着石子,一边唱着一首谣曲: 锣鼓响,脚底痒, 越剧小姐妹来下乡; 丝竹起,幕布开, 八十岁阿奶变小孩 油炸年糕片的香味伴着谣曲随风飘飞,村口小店里一桌麻将正搓得兴浓,有人忽地住了手,狗一样嗅着鼻子,抬头往大樟树底下张望。 细毛,那人喊道,来,来。 细毛恰好踢进一粒石子在前面洞里,得了一个胜局,听见叫声,一蹦一跳跑了过来。 麻将桌上堆着四堆钱,细毛对喊他的那人说,三舅,你面前的钱堆得像一座小山哩,你赢钱了,你把人家城里打工挣的钱都赢走了,你买上海奶糖给我吃哩。
三舅拣出一张碎票,说,买什么上海奶糖,一早起来我还没吃东西哩,我买你的油炸年糕片吃。 细毛就把衣兜裤兜里装的油炸年糕片兜底儿倒在麻将桌上,随手抓过那张碎票,让老板娘店里称了半斤上海奶糖,一溜烟跑回大樟树底下来。 一路跑细毛一路喊,二辫,二辫。 一个黑黑胖胖的妮子迎了上来,把衣襟掬成一个大兜。细毛把半斤上海奶糖一颗不剩全倒在那个大兜里。
二辫说,细毛你数一数有多少颗,我给你分配。 伢儿一窝蜂拥上来,眼睛滴溜溜地盯着二辫衣襟里的奶糖。 细毛数完了,说,三十八颗。 二辫想也不想,说,我们一共七个人,每人分五颗,五七三十五。剩下三颗,细毛加一颗,我加二颗。
大家有没有意见? 伢儿们都说没意见,细毛也没有意见。二辫是村支书的小妮子,应该多加二颗。 锣鼓响,脚底痒, 越剧小姐妹来下乡; 丝竹起,幕布开, 八十岁阿奶变小孩 山风送着稚声童气的谣曲,谣曲里伴着上海奶糖的甜香。一会儿,谣曲停了下来,一个伢儿问道,细毛,你阿爸咋舍得把苍耳给杀了,苍耳长得多漂亮呀! 细毛踢石子的脚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踢他的石子,头也不抬,说,我没问阿爸,这是大人们的事哩。 大人们都说,荷花是村里一枝花,苍耳是村里一条龙哩,把苍耳杀了多可惜呀。
那伢儿是个碎嘴,又说。 你咋叫我姆妈名字呀!细毛把一颗石子踢偏了,踢到了洞外。农村里伢儿们吵闹,叫起对方父母的名字,就算骂到顶了。细毛刚想发作,回头又觉得人家毕竟是在说姆妈和苍耳的好处,就把一口气咽了下去。上前推了那伢儿一把,说,你知道什么呀! 那伢儿偏不买账,说,你阿爸心狠哩。
你阿爸才狠心哩!细毛这次真的恼火了,狠声回敬了一句。细毛知道阿爸杀苍耳是没有办法,阿爸给苍耳一次称了五斤连一片肉都没剔过的骨头,用绍兴酒在锅里煮熟。苍耳啃完五斤黄酒煮的肉骨头,就明白主人的意思了。苍耳是只通灵性的好狗哩。阿爸给它脖子上套麻绳索子,苍耳一点没有逃跑的念头,白茸茸的眼圈里,眼泪一颗颗往地上滴。
姆妈躲在东厢屋里呜呜地哭,奶奶在西厢屋里哭。 一阵山风吹来,沙粒打在细毛脸上。细毛的眼眶里眼泪在打转,他狠狠地瞪着那碎嘴的伢儿,说,哼! 出门约伙伴们来大樟树下踢石子前,阿爸姆妈拉着他的手,再三叮嘱了。奶奶的事儿是狗肉烂在肚子里屙在粪坑里,死也不敢说哩。 可那伢儿实在太嘴碎了,真不该约他来踢石子哩,细毛在心里窝囊得没有办法。
到底二辫忍不住,说,好啦好啦,细毛阿爸杀狗是为了奶奶哩。细毛奶奶都快要死了,有事求我阿爸帮忙哩,就把苍耳杀了,把狗身上的宝贝和两条后腿送给我阿爸了 正说着,大樟树上唿啦啦一声响,把树下一群伢儿都吓了一跳,仰起脖子看时,却又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只有山风吹动枝叶的沙啦沙啦声。那只日复一日高高搁在大樟树桠杈上的铁皮喇叭,差不多掉光了黑漆,还瘪了好几块。 午后的阳光暖暖地照耀着,透过树隙,星星点点照射在黑漆铁皮上。 细毛没有料到二辫就这样轻易地把应该烂在肚子里屙到粪坑里的事情说了出来,村支书就应该收人家的礼吗?二辫真是不害臊。
但二辫给他解了围,细毛心里又恼不着她。 一脚左,一脚右,三脚四脚前边边跳。一群伢儿又踢起石子来。 锣鼓响,脚底痒, 越剧小姐妹来下乡 大樟树桠杈上的黑漆铁皮喇叭发出一阵响亮的拉木锯一般咝啦咝啦的声音,然后呀地一声唱了起来。 伢儿们一个个伸着细长的脖子仰望着,像一群长脖子呆木鹅,一动不动。
温暖的阳光点点斑斑映照在破瘪的黑漆铁皮喇叭上,满树枝叶悄然无声地在风中摇曳着。 喇叭的声音沙嘎嘎的,却是久久不见的嘹亮,几片黑漆铁皮从喇叭上剥落下来。 喇叭里播放着一段越剧,是梁祝里的《十八相送》。梁山伯与祝英台杭城读书三年同窗,却不识祝英台是红妆女子。喇叭里,祝英台正一口一声地骂梁山伯是呆头木鹅。
玉水河畔的人都是听着唱着越剧长大的,细毛不但知道《十八相送》,还知道《楼台会》哩。 四下里霎时间都变得安静了,三舅他们停下手中的麻将牌,往大樟树这边张望着。老板娘倚在小店门框上,几片瓜子壳停留在她嘴唇上。 财旺老爸挑着一担空粪桶急急忙忙从村外走来,他儿子封手紧紧跟在后面,手里用草绳提着一捆青菜。山风把财旺老爸的一对空粪桶吹得灯笼似的晃荡着。
两人一眨眼来到大樟树下,向树上的黑漆铁皮喇叭张望着。过一会儿,财旺老爸卸下肩上的空粪桶担子,用手背把鼻尖下两滴清涕抹到了鞋底上,衣兜里掏出一支香烟来。 财旺老爸把浓浓一口烟吐出来。多久没听喇叭响了哩财旺老爸咕哝着,烟雾围着他花白的脑壳转圈圈。 细毛说,二辫,踢石子吧。
二辫嚼着上海奶糖,嘟嘟地说,姆妈来了。 细毛顺着二辫的目光望过去,一群年轻的妇女正走上玉水河岸,往村里走来。她们手挽的竹篮里有刚洗干净的衣衫,或者是几棵水嫩的青菜,一块精瘦的猪肉。 年轻的姆妈们一会儿都来到大樟树下面,仰着漂亮的脖子看一会黑漆铁皮喇叭,又听了一会《十八相送》,这才各自拉过自己的伢儿,拍打着他们身上的泥土。那个碎嘴的伢儿被他姆妈剥下粘满红土的罩裤,里面的青布棉裤难看地裸露出来。
看你都玩成泥猴子了。姆妈在他的身上扑打着,说。 那伢儿瞥了细毛一眼,目光中有责怪的意思。 细毛嗫嗫地说,是我阿爸姆妈让在这儿踢石子哩。 年轻的姆妈一齐转过脸来,瞅着细毛,把细毛的脸瞅成了两块红布。
细毛轻轻扯一下二辫的衣袖,说,二辫 大樟树桠杈上的喇叭里,祝英台开始给梁山伯做媒。梁山伯唱,贤弟替我来做媒,但未知千金是哪一位?祝英台接着唱,就是我家小九妹 二辫站到姆妈们中间,大声说,是我让细毛通知伙伴们来踢石子的,我们等着听细毛奶奶唱越剧哩。 二辫给细毛打了掩护,但她的话让大樟树下的人都吃了一惊。除了细毛和二辫,还有二辫姆妈,这里再没有人知道事情真相了。 年轻的姆妈们看一眼二辫,又瞅了一眼细毛,最后一齐把目光转向二辫姆妈。
二辫姆妈轻轻给了二辫脑袋上一个爆栗子,说,嘴上不加锁的死妮子。 财旺老爸把烟屁股在鞋底上摁灭了,说,大妹子可是一生胆小,她这是 这时,咿呀唱着的喇叭突然熄了。像突然间唱响起来那样,让樟树下的人们又吃了一惊,一齐仰起脖子来看。 喇叭里响起一声有力的咳嗽。 村民同志们,刚才大家都听到了十八相送,那是戏里人唱的。
这是给大家静场哩,啊。喇叭里一个声音响亮地说。 二辫瞟了细毛一眼,细毛咧嘴笑了笑。他明白二辫的意思,那是她的支书阿爸在喇叭里讲话哩。 支书说,我们村老婶子好了一辈子越剧,没给任何人唱过一句戏哩!啊。
老婶子这一生有一个愿望哩,她要给全村人唱一嗓子 支书的声音小了下来,田塍,荷花,扶好了老婶子,给你们半个钟头,啊。 细毛的脑子里浮现出这么一幅画面:支书从话筒前扭过脸来,像小学里老师布置作业那样吩咐阿爸姆妈。阿爸和姆妈一边喏喏答应,一边搀扶起病重的奶奶,来到话筒前。奶奶硬撑起身子,激奋得连满脸的皱纹都通红了。 远处飘过来一朵浮云,遮住了太阳,村子里一下阴暗下来。
山风沙啦沙啦吹动着大樟树的枝叶。 财旺老爸吐了一口痰,说,大妹子呀,没想你临老倒老出胆气来了哩。 大樟树下年轻的姆妈们一锅粥似地吵嚷开了,叽叽喳喳,谁也听不清她们在说些什么。 那个碎嘴的伢儿上来擂了细毛一拳头,说,细毛你能哩,哄我们来踢石子,请我们吃油炸年糕片,吃上海奶糖,原来是让我们到村口听你奶奶喇叭里唱越剧哩。 细毛嘻嘻地笑道,看了二辫一眼,二辫咕咚一声把半块上海奶糖咽了下去,格格格笑起来。
正闹着,村街里拐出支书来。支书背着手,大?L着腿杆子走过来。 年轻的姆妈们一齐住了嘴,财旺老爸对封手使个眼色,封手把手中青菜往地上一撂,连忙挑起臭烘烘的空粪桶担儿,远远地放到一堵矮墙底下去了。 支书踏踏地走到樟树底下,眯起眼瞅树桠杈上的黑漆铁皮喇叭。 喇叭里飘来一阵压抑的咳嗽,然后是细毛姆妈荷花轻轻的声音,婆婆,你先喝一口水。
支书冲着喇叭骂了一句,说,这个老婶子,真是个怪人。 财旺老爸说,支书你可是做了一桩善事哩。 年轻的姆妈们纷纷说,是哩,支书积了善德哩,叽叽喳喳又闹开了。 小店那边,三舅扯嗓子叫道,支书,过来抽支烟呀。 村支书冲小店那边挥了挥胳膊,自己掏出一支香烟来。
三舅觉得有点失面子,大声说,支书,田塍送你一根狗?抛樱?憔腿萌思页?敫鲋油罚?阋蔡??恕 种树不种树根种树梢梢,啊,你小子颠倒个头骂我哩。支书用打火机点着了香烟,吸了一口,骂道,你们辛辛苦苦打工挣点钱,全扔在麻将桌上了,啊。我一个电话让派出所逮了你们去,信不信?啊。 三舅笑嘻嘻说,男人的钱不扔在牌桌上,就扔到人家女人身上了,扔到人家女人身上就影响和谐社会哩。 三舅的话被喇叭声打断了,喇叭里响起奶奶清嗓子的声音。
二辫姆妈说,都别吵吵了,荷花她婆婆要开唱啦。 喇叭里却又静寂下来。 山风一阵阵从村外的丘坡上刮过来,褐红色的土粒打得人脸上疼。 终于,喇叭里响起一个哀怨的声音,奶奶捏着嗓子,唱,梁兄啊 细毛一下就明白奶奶唱的是《楼台会》,当呆木鹅一般的梁山伯终于得知祝英台是个女扮男装的痴情女子时,祝英台早已被狠心的父亲许配给了马文才。 奶奶悲戚的唱声戛然而止,喇叭里传来椅凳翻倒的响声 那朵浮云渐渐变得厚重起来,久久地遮挡着太阳,大樟树下显得更加阴暗了。
山风呼呼地掠过村子上空,樟树的枝叶沙啦沙啦响着。 财旺老爸走过来,用他粗糙开裂的手掌,在细毛脑壳上抚摸了一把。 支书吐出一口浓烟,嘟哝了一句,到底撑不到半个钟头哩,啊
- 北师大版数学四年级下册3.4包装
- 第19课 我喜欢的鸟_第一课时(二等奖)(人美杨永善版二年级下册)_T644386
- 北师大版八年级物理下册 第六章 常见的光学仪器(二)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 冀教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第二单元《有余数除法的竖式计算》
- 外研版八年级英语下学期 Module3
- 冀教版小学英语五年级下册lesson2教学视频(2)
- 二年级下册数学第三课 搭一搭⚖⚖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其五)》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江苏省
- 《空中课堂》二年级下册 数学第一单元第1课时
- 沪教版牛津小学英语(深圳用) 四年级下册 Unit 2
- 【获奖】科粤版初三九年级化学下册第七章7.3浓稀的表示
- 苏科版数学八年级下册9.2《中心对称和中心对称图形》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泊秦淮》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辽宁省
- 第五单元 民族艺术的瑰宝_15. 多姿多彩的民族服饰_第二课时(市一等奖)(岭南版六年级上册)_T129830
- 二年级下册数学第二课
- 七年级英语下册 上海牛津版 Unit3
- 北师大版数学四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第四节街心广场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泊秦淮》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广东省
- 外研版英语三起6年级下册(14版)Module3 Unit1
- 3.2 数学二年级下册第二单元 表内除法(一)整理和复习 李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