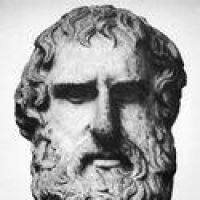吴若增
/文学
麻 雀
作者:吴若增
麻雀实在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它们不怎么美丽,却也不怎么难看;不怎么乖巧,却也不怎么讨嫌;它们似乎永远不可能繁殖得蝗虫一般铺天盖地,却也似乎永远不可能被淘汰得销声匿迹……特别是——在跟咱们人类的关系问题上,它们似乎铁定了永远不会靠近,却也似乎铁定了永远不会疏远。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大跃进”生活过来的人们肯定都还记得,在咱们这里,它们曾被宣布为害虫,受到过全国共诛之全民共讨之。奇怪的却是,在今天看起来,它们的数量虽不见增加,却也没见减少。而且尤其令人不解并令人感动的又是,它们似乎并没有计较人类的恶意,并没有因此而疏远人类。
对此,我曾经以为这是因了它们的生性宽容,或索性就是没记性,写这文章时才想到:它们之所以如此,其实倒可能是因了它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咱们会把它们宣布为敌人! “你们活你们的,我们活我们的,我们又不曾去抢你们饭碗里面的粮食,凭什么你们要把我们当成敌人呀?”它们一定是这样地想。 便是当年咱们爬上房顶,呐喊放炮,敲盆狂叫,累得它们一个个从天上掉下来,它们奄奄一息之时也一定不会想到谋杀,而只会想到:“这人……怎么都疯了?” 是的,人要是疯了,就易于把面前的一切都看成敌人,且斗争起来不择手段。 我在乡下时,曾经干过上房揭瓦掏麻雀的事——罪过。罪过。但我当时的动机,却不过只是想要试一试能否把它们驯化。
我就发现,成年的麻雀是不可能被驯化的,它们情愿死也不会投降,更不会叛变——真的,我就不曾发现过一个“雀奸”。想起它们被我关在笼子里时的眼神儿——愤怒的抗争的时刻准备拼死一搏的刀子一样的眼神儿,我至今都心有余悸。而且,想起我亲眼看到过它们宁愿饿死,也不肯吃上一粒我撒在笼子里面的粮食时,我对它们的敬意都至今不减。 “这是怎样的一种刚烈的动物呀?”常常地,我这样想。 “不自由,毋宁死”——这誓言,在麻雀们的身上,我看到了最最完美的体现。
是的,麻雀们就是这样的一种酷爱自由的家伙。别看它们跟你生活在一起,你却是永远也不可能剥夺它们的自由的——不。不对。不能把它们理解为是跟咱们生活在一起。因为表面上看起来仿佛如此,而实际上却是跟咱们不远不近、若即若离。
至于本质上到底是怎样的呢?本质上是它们根本就没有进入咱们的生活——或者说,它们根本就没有打算进入咱们的生活。 这倒令我忽地有了一点明白:距离这东西,常常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这就比方说咱们人,有些人离得很近,但关系却其实很远。 远就远吧。只要它们不伤害咱们,它们就有生存的权利。
这不是个宽容不宽容的问题,这是个观念的问题。在这问题上,咱们人不是已经进化到了这样的一个观念了么:所谓现代人权的核心,就是只要你不伤害他人,你就有你按照你的方式存在的权利,不管你的生存方式与别人的生存方式有着怎样的不同。而且,也只有抱了这样的观念,社会才能真的多元,而人与人也才能真的和谐。君不见在咱们这样文明的都市里,自从咱们承认了麻雀具有生存权之后,人与麻雀才渐渐地达成了和谐么? 与人相比,麻雀算是弱势群体。对于弱势群体,仅有同情是不够的——我甚至要说,同情其实是个错误。
这就好比人们对待农民工,想起来就同情一下,想不起来就惯性地歧视,这其实并不公平。倘若你能够认识到人与人本来平等,你因此就能够以平等之心去对待,那就无所谓谁去同情谁了——凭什么人家要你去同情呀?人家凭力气吃饭,又没来抢你的饭碗,你同情得着么? 关于麻雀,可说的正多,限于篇幅,就此打住。最后我要说我有个疑惑,疑惑于都市里的麻雀们夜里都在哪儿睡觉呢?它们总不至于像是某些人那样白天在市里上班,晚上开车去郊外住别墅吧?幸运的是,就在最近的几天,我终于有了发现。那是我的窗外竖着一支灯杆,灯杆的顶端安放着一只倒扣着的锅形路灯。那路灯因在小区,便有几分美丽,且宽阔,想不到竟被三只麻雀看中,作了它们的巢。
每天,看见它们在那里进进出出,常要令我笑起来,心想麻雀这东西真的是一种聪明的动物呀。冬天住在那里,既安全,又温暖——那灯不就是暖气么?反过来说,在这个由人称霸的生活空间里,能够寻找到这样既安全又温暖的窝还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呢。 只是,我又确定地发现:它们进进出出的时候,事先总要在那灯杆附近的树枝上徘徊许久,或从窝里伸出半个脑袋观察许久,等到确定了没有危险,这才进出它们的家。 于是我始明白:咱们现在与麻雀所达到的和谐,还缺少一个信赖,还只是初级阶段。(今晚报2006-12-30)
- 沪教版牛津小学英语(深圳用)五年级下册 Unit 1
- 人教版二年级下册数学
- 河南省名校课堂七年级下册英语第一课(2020年2月10日)
- 3.2 数学二年级下册第二单元 表内除法(一)整理和复习 李菲菲
- 冀教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第二周第2课时《我们的测量》宝丰街小学庞志荣
- 第五单元 民族艺术的瑰宝_16. 形形色色的民族乐器_第一课时(岭南版六年级上册)_T3751175
- 七年级英语下册 上海牛津版 Unit9
- 沪教版八年级下册数学练习册21.3(3)分式方程P17
- 沪教版八年级下册数学练习册20.4(2)一次函数的应用2P8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泊秦淮》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湖北省
- 30.3 由不共线三点的坐标确定二次函数_第一课时(市一等奖)(冀教版九年级下册)_T144342
- 第五单元 民族艺术的瑰宝_16. 形形色色的民族乐器_第一课时(岭南版六年级上册)_T1406126
- 冀教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租船问题》
- 沪教版牛津小学英语(深圳用) 四年级下册 Unit 2
- 冀教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第二单元《有余数除法的简单应用》
- 冀教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第二单元《余数和除数的关系》
- 第4章 幂函数、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下)_六 指数方程和对数方程_4.7 简单的指数方程_第一课时(沪教版高一下册)_T1566237
- 第8课 对称剪纸_第一课时(二等奖)(沪书画版二年级上册)_T3784187
- 冀教版英语三年级下册第二课
- 北师大版数学 四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第二节 小数点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