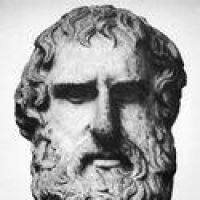彭兆青
/文学
女岩神祭
作者:彭兆青[怒族]
一 重重山岭,层层峰峦,拥抱着隐藏在滇藏交界附近的葫芦寨。 葫芦寨像个半大不小的葫芦,寨尾那条小河,时而奔向深渊,时而隐没于密林草丛间的驿道。这条驿道是葫芦寨唯一通向山外世界的路径。 葫芦寨是一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同样也是各种神灵鬼怪主宰一切的特殊地块。这里几乎所有的峰峦悬崖、河流山川,甚至每块怪石、每棵古树,都有庇护它们的神灵。
几千年传下来的风俗,崇拜神灵鬼怪仿佛得到这块古老神奇土地的养育和优待。 二 江娣捧着一颗虔诚的心灵,诚惶诚恐毕恭毕敬跪拜在搭在寨前台地上的祭神台前。她微微抬起一双带着些许迷茫困惑的泪眼,敬畏地望着摆在祭神台上的祭品,便脸热心跳地闭上了双眼。此刻的江娣,就像要上屠宰场的小绵羊,任凭神灵宰割处置她的灵肉了。 她刚满十六岁。
按照葫芦寨习俗,凡是女人第一次更衣(注:更衣:怒语直译,特指妇女经期。)到出嫁前这段时间内,要祭神一次。今天,阿妈逼着她去祭神,不由她不去。 她长这么大,尽管祭神台就在寨前山坡上,但她从来没有来过。葫芦寨的规矩,未成年的女子不得不上祭神台,否则亵渎神灵,寨子就会大难降临。
阿妈呀十六岁的江娣不禁倒吸一口气,失声尖叫起来。她的心脏怦然悸动,全身血流骤然加快,竟忘了阿妈叮嘱多遍的祈祷词。 克莱大姐,你死得好惨呀!不知怎地她想起了因难产暴死的大姐,便呐呐说出这没头没脑的话来。两年前大姐遭难产暴死的情景历历在目:没有生气没有弹性变得僵硬的大腿之间夹着一截已不会动弹的小脚丫变成了祭神台上那个庞然大物。 罪孽啊罪孽。
她生怕亵渎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祭台,惊恐地闭上眼睛,双手合十,从抖动不安的嘴唇间嘣出了祷词:请饶了我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女岩神她念着,串串晶莹透亮的泪珠,洒湿了祭神台下被善男信女踏得光滑溜平的泥土。 她不敢得罪这个女岩神。 不知有多少个世纪了,葫芦寨人对这个传说中的守寡经不住寂寞的女岩神,又敬又畏,惟恐冒犯她,被她收去魂魄,给全家带来灾难。尤其是那些身强力壮的后生伙子,更比别人多了一层畏惧,他们时时小心谨慎,生怕被女岩神看中,成了压山丈夫。从阿祖的阿祖们开始,葫芦寨的男人总是比女人少,尤其是那些年轻英俊的男人,寨里几乎每一年都要死一两个。
那个能卜卦算命、请神打鬼的纳姆萨(注:纳姆萨:怒语,指祭师巫师之类打邦跳神祭鬼的人。)揭开了奥秘:岩神是一个守寡多年的女神,凡是死去的青年男人,都是被受不住寂寞的女岩神抓去当夫爷了。 自古葫芦寨有个规矩:寨里的女人一律不得嫁往山外去,否则就会暴亡夭折,因女岩神不能容忍她管辖地段内的女人嫁到山外去。纳姆萨解释了这一千古之谜:女岩神犯了嫉妒病!人们背后悄悄骂女岩神,尤其是那些想嫁往异地他乡的女人们。 寨里的女人不能嫁出去,山外的男人不敢贸然进山当女婿。
倒苦了葫芦寨的子民们,三十几户人家,家家户户都是近亲近邻亲而又亲的亲缘关系,就像山里的野葛藤,理不清扯不明地蔓延繁殖了一代又一代葫芦寨人。 但葫芦寨的男性公民们庆幸的是:他们的身子一代比一代矮小,人的智力一代更比一代痴愚。他们还自豪地说:瞧我这个样,恐怕女岩神看一眼也烦心烦脑的了。她还会找我的麻烦? 葫芦寨的女人也多少庆幸自己的好命:反应迟钝,身材矮小,山外人对她们视而不见这反而成了葫芦寨女人自我安慰的良方:这辈子就不必担心成异乡的短命鬼了。 但江娣除外。
她长得娇小玲珑丰满,充满了诱人的妩媚。山里人说:漂亮的女人不聪明,聪明的女人不漂亮。这话对江娣是不适用的。山外来的人都说:山里女子的聪明和漂亮都统统集中在江娣一个人身上了! 此刻,江娣正想痛痛快快大哭一场,为已经进入成年女性的自己,为自己前程未卜的未来。 阿妹,你应该到山外去生活。
像你这样漂亮的姑娘不应在此虚度自己的一生。阿妹,跟我远走高飞吧。那个来自山外的年纪轻轻的阿山哥,不止一次地说。 可是江娣又仿佛听到来自遥远天国的一阵尖厉吼叫声:谁敢嫁到山外去,我就让她死,让她死,让她死她不禁毫毛倒竖地吓出一身冷汗。 三 从祭神台回来,满腹心事的江娣没有力气顾脚下的坎坎坷坷了。
呸!是谁这样没良心。正在想心事的江娣突然停下来,神色慌张的颓然瘫坐在一滩不知什么液体浸渍了的地边。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上,散发着一股尿臊气味。 上红更衣后的女人,千万跨不得男子刚撒过尿的地方。阿妈曾在她第一次上红更衣的时候说。
为什么?怕怀孕呀。你见过为此怀孕的吗?阿祖阿奶都这样说,哪个女人想自找麻烦与自己过不去? 唉,倒霉透了。去祭神偏偏碰上这晦气,肯定是女岩神惩罚自己,叫我怎么办呢?她害怕得捂着发红的眼哭了。哭了一会,她用牙把嫩红的嘴唇咬住,不让恶毒咒语冲出口来。 嗯?说不定是牛马撒的吧?她怀着一线侥幸的心理想道。
要是这样,我就不必担惊受怕了。 嗨。想到哪儿去了。谁说不是寨子里女人们撒的呢。她噗哧地笑了起来,抬头望了望没遮没拦的四周,蹲下身在它一旁也撒上了一泡尿。
她蹲在一旁看着这两滩尿渍,比较着它们圆圈的大小差异,想象着男人们尿渍的形状该是什么样子。半晌,掩起羞赧发烫的双颊笑着朝家里走去。 四 平时从屋里外都可开关的门闩纹丝不动了,江娣见门从里顶死,想也没想使力摇晃起来,把个小小木楞房的门扇摇得嘎吱嘎吱乱响。 屋里传来一阵唰唰唰的响声,江娣妈双颊微红开门了。江娣跨进去后,不由扫视屋内。
只见常来串门子的老鳏夫达西悠闲自在地坐在火塘边,端着轻轻摇晃的盛满咕嘟酒(注:咕嘟酒:怒族民间用包谷面煮熟后酿出的酒。)的大木碗,抬头看了江娣一眼,又忙着喝了一口。 达西是江娣的远房姨爹,身边有一个叫格当的痴呆儿子。这位远方姨爹喜欢有事无事来家串门子,每次来总见阿妈拿酒拿笑招待他。江娣伶俐,可猜不透其中奥妙。
她一眼瞧见阿妈零乱不堪的衣着和那副慌乱不安的神色,心中产生了异样的感觉。她又一次抬起迷惑不解的眼睛,看了看大白天关在屋里的两个老人。 被咕嘟酒的后劲搞得神魂颠倒的达西,眯着混浊的眼睛,上上下下把江娣看了个遍,目光停在江娣那隆起的胸脯上。江娣被盯得浑身像被虫咬似的不自在。达西摸了摸乱蓬蓬的锅盖头,捋了捋下颔焦黄稀疏的山羊胡,像是发现什么新奇事物似地说道:呀,好你个江娣,都长成该找男人的身子了,跟我家格当倒是天生地配的一对。
你格当哥也到了该套金鞭子的年龄了,江娣,你可要死死套住你格当哥的脖子呀!说到这里,喷一口恶臭酒气,嬉皮诞脸地盯着江娣。
谁稀罕你那个傻子格当,看他那个拳头大的矮疙瘩,还有什么脸讨媳妇。真要讨,讨着寨头的哑巴姑娘娜白也算不错了。江娣顶撞起来。什么金鞭银鞭的,羞死人了。想起格当那傻乎乎专盯年轻女人胸脯的丑态,和挂鼻涕淌口水的一副窝囊相,江娣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更不要说是嫁了。
她心中只有那个从山外飞来的雄鹰赶马做生意的阿山哥。 江,别没大没小的使性子,看别人笑话,人家是你姨爹呢,怎么能这样。呆在一旁的江娣妈出来圆场了。轻轻骂了江娣一句。 阿妈,你别总是向着他,什么套不套的,我就听不得这般难听的话。
江娣还是不依。 江。你少说一点好不好,谁也不会把你当哑巴卖的。江娣妈白了女儿一眼。 好了好了,我不说了,留着你们独个儿说吧。
讨厌。江娣呼地从火塘边上弹起,咚咚咚几步跨出门去。在双脚跨出门外的一瞬间,顺手砰的把木楞子房门甩得震响。 唉,如今年轻人像是吃多了辣子火气大得很哟。尴尬的达西慢悠悠站起身,好了,我也该走了。
女大不由妈,翅膀硬了,手膀粗了,只好随她们的便罗!达西像是说给自己又像是说给江娣妈听。 人走屋空,江娣妈兀自伤心得直掉眼泪,泪眼朦胧地凝视着刚才与达西偷偷温存亲热过的还未收拾的地铺发呆 五 夜深了。燃在点火架上的松明火把孤零零摇曳着,忽明忽暗的火光照亮了忙着绩麻纺线的江娣母女俩。 江,你格当哥送来酒了。 送酒? 江娣妈叹了一口气:唉,人家可是冲着你呐。
冲我?江娣莫明其妙地睁大了神采飞扬的双眼。 你呀,连人家给你下聘礼都不知道,你是有意假装的吧?江娣妈停下手中的活,点点江娣刘海盖住的前额。阿妈,你舍得我走?江娣有点悲哀。 唉,有啥办法呢?女儿是养给别人的,哪能一辈子留在阿妈身边。江娣妈说,你十六岁了,该找个男人了。
女人女人,只有嫁了男人才算有了依托,有了靠山。 我不,我偏要守着阿妈,谁也不嫁。江娣撒娇地扑在阿妈怀里。 阿妈想过了,你格当哥虽说傻一点,但你要看到他家的财产。俗话说:聪明的女人看家产,糊涂的女人看模样。
独眼珠似的一个儿子,所有的家产牲畜谁也不来挨你争啊分的。 我不嫁,我不嫁!江娣把头摇得如飞转的磨盘一般。 为什么? 我还小。 哟,我的江,妈在你这个岁数已当上妈了。 不,我不嫁人,我也不想当妈。
江,你就听妈的话,答应嫁给格当哥吧! 不。我不嫁,任谁也不嫁,就是把脖子砍成九段也不嫁。要是你想嫁,就嫁给他们一家子好了。呜呜她发觉自己赌气说漏了嘴,只有以哭来掩饰,等着阿妈斥责。 女儿的话像一颗针戳痛了江娣妈的心灵,手中的线团咚地掉在地板上。
她没有发作,只把呆滞的哀怜的目光久久扫在女儿身上。她觉得自己愧对女儿。 时间似乎凝住不动了,屋里异常寂静。 江。隔了一阵,江娣妈见到女儿那道歉的目光,心里平静许多,轻轻问道: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看上了山外的 在葫芦寨的人看来,火塘上那三块支锅用的石三角,就是野外神灵鬼怪安插来监视人间的耳目,因此,任何时候都要避免在火塘边谈论忌讳的事。
江娣妈恐惧极了,木然地呆望着那三个深深插在火塘上的石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六 一轮圆月高高悬在夜空,泻下满天满地满山的银色。已是凉爽的秋季了,天空显得格外湛蓝。江娣和阿妈依偎着坐在空地上的包谷杆上。江娣妈一时拿不准要说什么,机械地抚摸着女儿那张黝黑俊俏的脸庞,不由轻轻啜泣起来。
江娣见阿妈伤心抽泣,也禁不住哭了。 江。你是不是看上了那个山外来做生意的阿山?江娣妈蓦然间问了一句。在这空地上,什么内心话都可以说的。 嗯。
江娣温顺地点点头。 一声轻轻地嗯,江娣妈听来如五雷轰顶,头脑一阵轰鸣,半晌说不出话来。 造孽啊造孽,纳拉戛布(注:纳拉戛布:怒族传说中天上最大的神王。)天神啊,这就是报应吗?江娣妈抬起失神的眼睛,高举着抖动不止的双手,仿佛在向苍天向至尊至贵的神王纳拉戛布在求援求救,一串串泪水从腮边滚下来。 江娣为了取得阿妈的支持、同情和谅解,顾不得少女的羞涩,跪下哀求说:阿妈,我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请你答应我吧! 想去找死喽!江娣妈想起女岩神的威严,想起葫芦寨千古老规矩,惊恐地搂住女儿。
江娣是很理解阿妈的悲痛的。阿爸在一次围猎熊瞎子的恶斗中一倒不起,姐姐又遭难产一去不回,母女俩相依为命到如今,眼下自己要远走他乡,阿妈已够伤心伤肝的了。 阿妈,那个傻里傻气的矮疙瘩格当我是死活不嫁的。女儿要嫁的人,葫芦寨还没生出来,你老人家就不怕女儿等白了头发,等老了皮肉吗? 不害臊的东西,尽说些不要脸的话。江娣妈忍不住自个也抿嘴笑了。
唉,只要你真心实意地爱上那个山外来的阿山,只要他愿来咱葫芦寨上门当女婿,阿妈也没有不同意的,怕就怕人家不愿。再说,既然已接下你格当哥的聘亲酒,要退婚,咱这葫芦寨还没这个先例。人们会戳脊指背的骂你咒你。 阿妈,谁叫你当初自作主张接酒,你一点也不为女儿着想。要我嫁他,明明就是害我嘛。
瞧他那傻样,让我怎么跟他过一辈子呀。你们再逼我,我就只有死了。江娣说着又哭了。 江娣妈心里格登地跳了一下。她完全听信达西的安排,与他偷偷摸摸吹了几次枕头风后,竟然鬼迷心窍地默认了格当和江娣的婚事。
吐出的口水舔不回,射出的竹箭收不回。痛悔不已的江娣妈,心头生出了难以言传的压抑感和一阵阵揪心揪肝般的扯痛。 七 焦心如焚的江娣总望着那条通往山外的驿道出神,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阿山哥。她和格当那不可抗拒的婚礼已定在这个月月亮圆的晚上。望着一天比一天复圆起来的月亮,江娣后悔当时没有跟着阿山哥出山。
她如饥似渴地盼着阿山哥,偏偏那条蜿蜒曲折的山路上不见他的身影,悠长悠长的峡谷听不到那令人心花怒放的马铃声。 在异常痛苦难熬的时日里,江娣回忆着和阿山哥相处的日子。 她与阿山相识不是一两天的事。当她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时,就常见那个长得眉清目秀的外地小伙子跟着他阿爸赶着牲口驮着盐巴茶叶来葫芦寨收山货。后来,他阿爸过世了,长得越来越高越英俊的阿山哥,隔三月半年的就会随着叮当叮当的马铃声踏进山里。
接触多了,她总佩服阿山哥口齿伶俐,总有说不完的神奇世界。这在山里是听不到的。听得越多,江娣更向往山外那个陌生和神奇的世界。 阿妹,请你再帮我割点马草吧。忙着收山货钉马掌钉的阿山说,还从马肚子下射出甜蜜的目光,总叫她心花怒放地答应了。
阿妹,你该到山外去走一走。 阿山哥,山外像咱葫芦寨吗?她忽闪着一双大眼问。 不。那可是另一个天地。他不无自豪地说。
- 青岛版教材五年级下册第四单元(走进军营——方向与位置)用数对确定位置(一等奖)
- 3.2 数学二年级下册第二单元 表内除法(一)整理和复习 李菲菲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泊秦淮》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辽宁省
- 外研版英语三起6年级下册(14版)Module3 Unit1
- 飞翔英语—冀教版(三起)英语三年级下册Lesson 2 Cats and Dogs
- 人教版二年级下册数学
- 三年级英语单词记忆下册(沪教版)第一二单元复习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其五)》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辽宁省
- 二年级下册数学第二课
- 北师大版八年级物理下册 第六章 常见的光学仪器(二)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 《空中课堂》二年级下册 数学第一单元第1课时
- 七年级英语下册 上海牛津版 Unit3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泊秦淮》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天津市
- 北师大版数学四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第四节街心广场
- 19 爱护鸟类_第一课时(二等奖)(桂美版二年级下册)_T3763925
- 外研版英语七年级下册module3 unit2第二课时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老山界》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安徽省
- 外研版英语七年级下册module3 unit1第二课时
- 第4章 幂函数、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下)_六 指数方程和对数方程_4.7 简单的指数方程_第一课时(沪教版高一下册)_T1566237
- 七年级英语下册 上海牛津版 Unit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