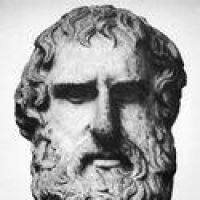母国政
/文学
羊 耳 镇
作者:母国政
一
爬犁像一只小船在没有尽头的雪地上越滑越远,有时像受到海浪的冲击,突然颠簸两下,然后又稳稳地向前滑行。 前方是一大片还挂着零星金黄叶子的白桦林,一排排银灰色的树干交错着,疏郎的枝条上挂着白雪,在清晨的苦寒中,像一幅冻僵的画儿。 土生知道,爬犁一冲进白桦林,就会消失,像树杈上的一片开始融化的薄冰,掉进没膝的积雪中。 他猛地向前冲去,但是两腿竟像被抽去骨头,软颤颤地哆嗦着,他几乎是原地不动地栽倒在白雪中。 他的好朋友黑眼圈儿敏捷地蹿过来,卷动着红舌头,向他脸上喷散一股股热气。
他推开黑眼圈儿硬邦邦的脑袋,抬眼寻找那架远去的爬犁。 爬犁快要钻进桦树林了,快要消失了。 一个沉重的声音在他心里响着:消失的不是爬犁,是妈妈她将永远消失了! 他看见妈妈从厚重的羊皮盖被中,艰难地扭转身子向他招手。那宽大的紫色袄袖在白雪世界里像一面小彩旗。不停地飘啊飘的,只是妈妈那张扑着白粉,涂着口红的脸,看不真切了。
但他像平日一样,能感受到那张脸上对他关爱至深的神情。 坐在妈妈身边的中尉,也扭转身子,向他挥动着军用绿手闷子。 土生,多多保重!一个星期爸爸妈妈就回来!妈妈的声音像一串串银铃,又清脆,又欢快。 他从雪地上爬起来,伸着细长的脖子,向妈妈望去。视野里,只是一片片白亮的模糊的光影他的眼睛,被泪水蒙住了。
黑眼圈儿像往常一样,听到妈妈的喊声,便要抢先跑过去。它竖起肥大的黄尾巴,飞快地向前蹿跃,细长的腰身忽直忽弯,四蹄刨起的碎雪,像一簇簇雪莲花。它追出去仅三五十米,前面的爬犁已钻进桦树林,只见妈妈那紫色的衣袖最后闪了一下,便消失了。它骤然停住,摇摇耳朵,怔怔地向前张望一会儿,突然凄哀地吠了一声,好像它也感到了某种伤痛。 土生只觉得心里最珍重的什么遗失了,空空荡荡,空得他发慌,发软,举手投足都没有什么力气。
同时他又觉得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充塞在他心里,分量那么沉重,也压得他发慌发软。他病了似的踩着被雪撬和车轮轧得坚实而平滑的雪路往回走,直到走回羊耳镇里,他也不知道一路上自己想些什么。只知道黑眼圈儿几次扬着毛茸茸的脑袋轻声召唤他;甚至将身子贴在他的小腿上安慰他,仿佛深知他的痛苦。 天已经大亮了。街两旁的店铺里飘出一股股浓重的灰烟,有的烟囱里飞散着暗红的火星。
伙计们有的在卸护窗的木板,有的挑着水从河边回来,有的举着木竿将衣物悬挂在店前的棚子里。 两个穿着光板皮袄的鄂伦春猎人正蹲在一家皮货铺子的台阶上抽着旱烟,身边的马上驮着猎枪,驮着兽皮。他们从山上下来,不知走了几天,来这里出售自己的猎物,然后购买粮食、白酒、子弹,甚至大烟土,再回到深山密林中去。 土生着意看了看那两匹马都是酱色的,个头很大,像是蒙古马。哈气在它们嘴边的毫毛上凝聚成霜雪,它们就像长了长长白胡子的老头儿。
土生突然想到,也许,我也应该找一匹马?有了马,就安全多了。马路得快,也走得远,也许用不了两三天,就可以驮着他和黑眼圈儿穿过白俄开办的农场,穿过大草原,到人们再也找不到的地方。 他身旁一家早点铺子的棉门帘子掀起来,有人在白蒙蒙的雾气中招呼他。 他看清了。小鹿和野中尉手下的警察小队长王玉成正咧着油乎乎的厚嘴唇冲他笑。
中尉和太太走了! 走了。 进来,吃俩?子,喝碗浆子,暖和暖和。我请客。 土生鄙视像王玉成这样的警察。中尉要求警察们都在饭堂里吃饭,这不,中尉刚走,他就出来打野食儿了。
他请客?他吃完东西都不给钱,怎么请? 我得上学去。 王玉成走出铺子,拉住他的手。 上什么学!太太出远门,你还不玩玩。晚上我带你掷骰子去,准保你赢三十五十的。 土生觉得自己的手被那只油腻腻的胖手攥着很不舒服。
他挣脱开,抬脚就走。王玉成要追上去,却见黑眼圈儿正竖起耳朵,不高兴地唔唔哼着,横在他面前。他在黑眼圈儿的脑袋上拍了一下,又钻进早点铺子里。 警察队在大街北头的一座大院子里,对面是一个白俄老头儿开的百货铺子。站在大门口儿的高台阶上,可以看见百米开外的额尔古纳河。
现在,白皑皑的积雪把宽阔的河道和两岸连接起来。河中间有一片两三亩地大的沙洲,夏天长满绿葱葱的芦苇和茅草,野鸭子在沙洲上飞上飞下,叫得震天响。王玉成每年秋天都瞪着亮晶晶的小眼睛说:那野鸭子贼肥,下酒才香呢!说着,还猛地一拉枪栓。可他不敢去打。人们都说沙洲中间有一条线,过了线就是俄国的地盘儿,人家开枪打死你,白搭! 土生走进院子里,饭堂正在开早饭。
负责打饭的警察们端着一个个水缸粗的绿瓦盆,将热气腾腾的高梁米粥和玉米面饼子打回宿舍去。 大师傅老孙头儿高声大嗓地招呼他快来吃饭。刚才他和妈妈、中尉已经吃过狍子肉丝热面条了,但他还是走过去,拿了一个贴饼子。就在他转身要走时,心思一动,乘老孙头儿没注意,他又拿了两个,赶忙揣在大棉袄里。他要攒些干粮。
妈妈临走的时候,怕他在饭堂里吃不饱,给他做了一些寿司,冻在后院的一口小缸里。不过,他需要的更多他要吃,黑眼圈儿也要吃。离开羊耳镇,在额尔古纳河岸边的大荒原上,谁知要走多久才能遇上人家儿!冬天有雪,有冰,渴不死人,但没有干粮,会饿死人的。何况,不吃干粮,人没有力气,遇上狠或别的野牲口,也会被啃成一堆骨头。 他得走,必须走。
妈妈待他很好,像对亲生儿子一样。他也爱妈妈。他不知道人家的亲妈是怎么对待儿女的,可他从心眼里认为这个妈妈就是自己的亲妈。要是没有中尉多好!他和妈妈就可以快快乐乐地生活了。固然,中尉从来没有打过他、骂过他,甚至没有对他说过一句重话,可是中尉那张冷冰冰的有时还透出杀气的脸,令他畏惧。
不只畏惧,有时还令他厌憎。警察们在羊耳镇上干的许多坏事,都是中尉指挥的;老师和同学们歧视他,排挤他,也是因为中尉。 他已不再是当年那个被沃子领回来的七岁的孩子,今年,他十五岁,就要高小毕业了,他明白了一些事理,也知道了一些日本军队、警察在中国土地上干的坏事在这座警察大院里,他听到的见到的就不少。 有时他觉得羞愧,觉得尴尬,在老师和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每当那时,他就茫茫然,不知如何是好。
怎么办?这个关系到人生的大问题,对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来说,是来得太早了。不过,在一次次深深的苦恼后,他终于明白,要变化自己的处境,他没有能力,他所能做的就是逃避。 他早就想走。机会总算被他盼来了。 他知道,这次妈妈和中尉去奈勒穆图,名义上是去看望妈妈的女同学志子,实际上是拜望志子的丈夫日本陆军省军务局的一位要员。
前天下午,他放学回家,看见妈妈正在收拾皮箱,两个箱子都塞得满满的,妈妈还把两支半尺多长的人参装进一个很讲究的木匣子里,他看出妈妈要出远门儿。 妈妈告诉他,中尉和她早已厌倦了北满清冷寂寞的生活,而且中尉也厌倦了军旅生涯。他们想通过军务局的这位要员,调回日本本土。如果可能,中尉要回他的故乡千叶县的山区,继续当山村小学教师。说这些时,妈妈非常高兴。
明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过平静的日子了。再也不必担惊受怕的。你呢,也能去千叶读中学了。 对中尉和妈妈这一重大决定,土生很吃惊,更让他吃惊的是中尉。 你老说,中尉以前是小学教师? 是很不错的教师呢!学生们都很爱戴他。
他对你们江老师的教学还不大满意呢。不过,他不许我跟你说。 土生十分奇怪,那个挎着长刀、撅着小胡子、总是冷冰冰的中尉,怎么会是一位教师呢?居然学生们还很爱戴他! 土生想,如果那位军务局要员,果然有这样的力量,那么他也要同妈妈去日本了。这事儿,他做梦都没想过。 他不愿想。
他不能够。 他必须在妈妈回来之前,离开羊耳镇。 七天,足够了。 去哪里?他不知道。流浪吧。
无家可归的日子。他经历过。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泊秦淮》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湖北省
- 沪教版牛津小学英语(深圳用) 四年级下册 Unit 2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逢入京使》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安徽省
- 二年级下册数学第三课 搭一搭⚖⚖
- 第12章 圆锥曲线_12.7 抛物线的标准方程_第一课时(特等奖)(沪教版高二下册)_T274713
- 沪教版牛津小学英语(深圳用) 六年级下册 Unit 7
- 外研版英语七年级下册module1unit3名词性物主代词讲解
- 沪教版牛津小学英语(深圳用) 四年级下册 Unit 12
- 河南省名校课堂七年级下册英语第一课(2020年2月10日)
- 外研版英语三起5年级下册(14版)Module3 Unit2
- 8.练习八_第一课时(特等奖)(苏教版三年级上册)_T142692
- 沪教版八年级下册数学练习册20.4(2)一次函数的应用2P8
- 外研版英语三起5年级下册(14版)Module3 Unit1
- 沪教版牛津小学英语(深圳用) 四年级下册 Unit 7
- 冀教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第二单元《有余数除法的竖式计算》
- 8.对剪花样_第一课时(二等奖)(冀美版二年级上册)_T515402
- 每天日常投篮练习第一天森哥打卡上脚 Nike PG 2 如何调整运球跳投手感?
- 人教版历史八年级下册第一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沪教版牛津小学英语(深圳用) 四年级下册 Unit 4
- 北师大版八年级物理下册 第六章 常见的光学仪器(二)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