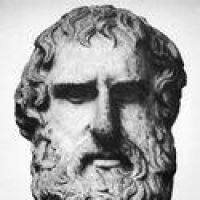景宜
/文学
骑鱼的女人
作者:景 宜[白 族]
雪山浮在茫茫的云海上,仿佛要随着缓缓移动的云朵一起飘去,不知要飘向哪里……也去做新娘吗?像我一样…… “呵!做了新娘!”我望着远处峰顶的白雪,眼睛花了,抽出手来揉揉眼睛,才又看清楚了身边的树木、山沟、茅草。我拉紧背绳,把背上的草垛往上抽了抽,一只手撑在一块大青石上慢慢站起来。背上的草垛子比我的头还高,我弯腰曲背听凭那沙沙作响的草墙压着我,脚步沉重地走下山去。 “做了新娘……”这个念头就像身后这条绵绵无尽的小路一直伴随着我。这些天来只要脑子里一闪出这个意念,不管是在众人面前,还是在背静处,我都会热血涌上脸颊,心儿咚咚地跳个不停。有时我自己躲着笑,对着镜子自己羞自己;有时也不知因为什么突然想哭。总之要不是我变了,就是人世变了,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起了一种变化,变得有点陌生、有点奇妙,让人隐隐地忧伤。 山洼石缝间开着一蓬蓬山茶花。这些我从小就看惯的花儿,突然不像从前那样水灵了,只是透出一片火焰般的颜色,使我想起一种热得使人颤栗的激情。“天哪!”我急忙用双手捂住脸,我不敢看那些花。半晌,慢慢松开手,又瞧见不远的山沟里,在冬天冒热气的山雾飘散开来的地方,露出几丛嫣红、粉白的山茶花,不知是隔着蒙蒙的山雾,还是隔着昨天到今天的许多事情,那水雾中的花丛就像蒙着一层恍惚的泪光,蒙着一层哀伤的影子。那些影子长久地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知道最初投下那些影子的是一双双眼 睛,那是昨天早上村里的姑娘、媳妇们在割草的山路上投射给我的…… “嗨!新媳妇,过门三天上山割草,婆婆不心疼,男人也不心疼吗?” “嘻嘻嘻,哈哈哈!”媳妇们笑开了。 “巴巴鱼,你心疼就来背我走一截好了,背到那棵老山林果树底下,来呀!”我对那个说话的女人说。 她生就一张扁圆脸,头发的高髻上插着一股银鱼飞簪。在村里的女人中她是最会讲故事唱调子的人。她一讲起故事来眉飞色舞,表情格外生动,讲什么像什么。她男人是大队会计,去参观过一次大寨。为此她在村前街上好夸耀过一些时候呢!她不会生娃娃,却爱在村前巷尾说点小话。有些想让会计批点地基盖房子的人,想开具证明出外做包工的人,就管她叫会计媳妇;那些记恨她的人却冲那张扁圆脸叫她“巴巴鱼”。 “呀!阿表妹,背你幺,要叫你男人来背嘛!”她看也不看我,朝一个媳妇笑着挤眼睛。 “哈哈哈……”女人们又笑起来。 “猪嘴!”我说了一声,拉起阿秀嫂就跑下山冈,绕过长满苔藓的大青栗树,穿过小矮山竹丛,沿着石头山路走向低处的山谷。 “瞧呀!瞧她围腰飘带上是金箔剪的鱼!”金花那大尖嗓门在后边喊叫。 “让我瞧瞧,让我瞧瞧!”一群妇女又追上来拽住我的衣裳角。 “哪里买的?也是婆家做给你的吗?” “呀!是金的,多漂亮呀!” “唉!一辈子能有几个漂亮的年头,难得呀!阿表妹。” “喏!她脚上的鱼鞋,还拖红尾呢!我年轻时候穿过一双是摇蓝尾,那时候红绸子难买得很!” 我被她们摆弄着,心里真不是滋味。怪我昨晚上看电影回来太晚,懒得上楼找衣裳,早晨随便穿上一件就上山来了。活倒霉!瞧她们那些眼光,亮晶晶的光泽里分明有羡慕、妒嫉和其它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也许女人看女人都是这样的眼光?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拘束,一时好像裤角也没有拉伸,围腰也系得有点歪;想伸手拉一拉又不好意思,想故作无事又十分别扭。这一刹间我肯定丑极了。 “哎!说来也是的!”巴巴鱼摘了一片叶子放在嘴边嚼着,身后的镰刀和背绳上的木扣子碰得叮当响。她摇晃着走在前面说,“要穿要戴就是趁年轻时候,做了媳妇就不要再想罗!不赶紧趁年轻时候穿,后悔来不及呀,金花!”她拍了一下身边的金花姑娘。 “嗨!我们穿不起!”金花一甩手穿过两棵小树,头也不回地说。 “这几年政策好,多做点活计少吃点零嘴,有哪样穿不起?只是莫一天憨头憨脑把几块卖刺菱角的钱也交给你那个老古董爹,自己攒着点,格晓得了?”巴巴鱼又拍了金花一下。 “哎,巴巴鱼,你钱多你咋个不穿呀?又不喂崽!”一个妇女问。 “穿?我年轻时候穿过多少,克钦地方的纱,越南地方的绸,你们呀!怕见也没见过!”她转过来用那白眼仁瞟了我一眼,一扭身又去嚼她的树叶子。 “哎!你们听,你们听,是哪几个人在唱?”金花姑娘俯身向菁沟里望。 深箐里的雾还没有飘散,像一泓蓝悠悠的水。雾中有节奏地传来“咚、咚、咚”的砍树声和粗犷的山歌。 “快瞧呀,快瞧呀!”金花拨开树枝指着下面叫,“是他们!是他们!” “死鬼,小心跌下去!”阿秀嫂一把拖住她的衣裳后摆。 “唱!唱一个跟他们比比!”阿秀嫂拍着金花叫,金花红着脸摇摇头。 “你唱!新媳妇你唱!你不是读得高中文化么,你来唱!”另一个小媳妇又来推我。 “唱哪调?”我有些犹豫。 “花上花。” “翠茵茵也行!” “唱呀!快唱!”妇女们七嘴八舌地喊叫。 没等我开口,巴巴鱼早在树丛中唱了起来: 小哥…… 采花要采叶子绿, 叶子又绿花又黄; 唱歌要找年轻伴, 莫约过时娘。 “哈哈哈……”妇女们笑得往树丛里钻,山箐里那几个唱歌的人也跟着大笑起来,惊起一群野山鸽在树林中飞窜,弄得树枝刷刷响。 “阿嘎!巴巴鱼,你哪阵子过时了,我咋个晓不得呀!再过几日你头上怕还要长出马屎菌的吧!哈哈哈!”我刺了那个扁脸婆娘一句,拉起阿秀嫂钻进了树林里。 我一边走一边心里自己跟自己打架:我是咋个了,刚才唱歌我怕什么?什么也没有怕呀!那犹豫什么呢?好像是一个小虫子不知什么时候咬断了我心中的一根筋,我胆怯了。就因为穿了这双鱼鞋,系了这条新围腰吗? 这么说,我变了。我从前可不是这样的。有一年去赶渔潭会,走到沙坪那两棵大青树下歇气,我听见一伙女人正在头碰头地悄悄嘀咕什么事。朝前一看,是巴巴鱼在眉飞色舞地比画着说:“……那海水是印度宝石蓝一样的颜色。那尾金鳞大鱼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神母的脚,她就有了神孕,十个月后生下了我们圣明的白王呀……” “啊!吉祥如意……”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群老大嫫口中连连祝福。 “噢!印度宝石蓝的海水……金鳞的大鱼……”我娃娃时候就和一群小伴听我阿太讲这个古老的神话。听过神话,我们那群野孩子常常把沙滩上的那堵大青石当成神鱼,比赛谁能骑上去!我为了爬上那块比我高几十倍的大青石,曾经跌得鼻青脸肿。我微笑着靠在一个老大嫫肩上说: “要是我呀,我要骑在那条鱼背上,走进印度宝石蓝的海里去……” 话还没说完,那群女人哗地乱开了,又笑又骂。有几个年轻的媳妇脸上绯红,好像触发了一种羞于启口的事情。老大嫫连忙堵住我的嘴:“说不得,说不得!哈哈哈!” 巴巴鱼白了我一眼,转身对一个老太太:“以后不知要出落成个什么东西呢!瞧她那副俏生生的眼眉,不是安分人。” 年龄还小,我听不懂她说的意思,但是我从心里讨厌她。到了前年我放农假回来,才算把她看透了。那阵子队上活计忙人手紧,安排不出人去放鱼鹰。我一听就乐了,伸手夺过了队长手中的竹竿。 “呸!”我阿妈一把拦住我,“男人放鱼鹰都嫌不安生,你姑娘家去放鹰,你有几张脸皮子?” 不等我阿妈说完话,我已经跑到海子边上了。我早就看上那个海阔天空的活计了。带一群黑翎的鹰儿满海子飘荡,想唱就唱,也没人管我,多开心的一台好事,比读书自在多了!谁知道又给巴巴鱼搅了一次臭水。那天我放鹰回来,见她在魁阁圆洞门下那间裁缝铺里指手画脚:“……不消说罗!就是她说的,要骑鱼呢……”裁缝铺里的那伙人阴阳怪气地笑着,就像耻笑一件丑事。 还没等巴巴鱼那张扭歪了的脸转过来,我“咚”地一声把长篙戳在地上: “你出来!巴巴鱼,你有几张嘴够我练拳头?出来!”我喊叫着把发辫往头上一勒,卷起袖子。 哪想她一斜身子,溜出门来拔腿就跑,一边跑一边喊:“要杀人了!杀人了……” ……太阳升高了。远远地看见山下的村庄像一堆小白石头。洱海水面上的白帆纹丝不动,好闷热哟!背上的草垛子越来越沉重,那尖茅草还戳得后脖子上热辣辣地又痒又痛。我用双手紧紧地拉着背绳,减轻一点肩上的压力。沿山路绕过一个岩子角,穿入了山环中的一块小盆地,猛然见一棵高高的山桃子树上,有一群白胸脯的小山雀在抖羽毛。瞧,它们梳理得多么惬意。我停住了,唉!瞧那些小雀子,它们一年四季漂漂亮亮,自由自在。它们也养儿育女,它们也做媳妇,就是不像我们这样烦恼。是的,烦恼! ……叫人烦恼的事发生在昨天下午。我跟阿秀嫂背着两大背茅草下山,就像两堵草墙在走动。 “喂!阿表妹,你等等!”阿秀嫂喊住我。 她跑上来背朝着我说:“快帮我把背子接下来,我去给你变一个把戏!” 我接住她的茅草垛,她一脱身钻进小树林去了,不一会举着一枝山茶花笑盈盈地跑出来: 嗨!多好的花呀!阿表妹!” “哎,给我一朵,给我一朵!”我从阿秀嫂手中夺过一朵山茶花来,往头帕边上插。 “嘻嘻嘻!”阿秀嫂拍着手大笑起来,“像哪个?像哪个?不像个老媒婆吗?哈哈!” “媒婆咋个?媒婆就媒婆,给你也戴一朵,你也做媒婆!”我说着就往她头上插了一朵红花,转身就跑。 阿秀嫂背起草垛子在后面追赶,一路用小石头打我。正嬉闹着,撞在前面一堵草墙上了,那个人转过身来: “你们瞧,新媳妇头上插了一朵大花,是谁给的呀!”巴巴鱼像见了鬼似的尖叫起来,前面的几堵草墙相继转了过来。 “呀!是他们丢给你的吗?”金花姑娘的眼睛亮晶晶的。 “什么是他们!你就知道他们!那你头上不也戴着花吗?”我撞了金花一下,走到她前面。 “金花和你不同呀!她是姑娘,你戴不合适,快丢了吧!阿表妹!”巴巴鱼笑着说。 “有什么合不合适的,满山都是花,我想戴就戴,管你什么事,你嘴又痒了么?”我盯着那张扁平脸。 “阿呗呗!好心你当成驴肝肺,你要戴你戴,我吃多了爱管你,你是我妈我姑奶?只不过是说我们青石庄女人的名声莫叫你这个搅世精给败坏了!”巴巴鱼嚷了起来。 “嘿嘿!我搅得了吗?我们大理苍山下九村十八寨的女人戴不戴得花不都由你管着的嘛!你天生就该管女人戴花不戴花!” “哈哈哈……”一群姑娘媳妇开心地大笑起来。 “呸!我走让你!我走让你!搅世精!”巴巴鱼一边骂一边用背上的草垛撞开人咚咚地朝前跑了。 太阳还没落山,我们走到村口,远远就看见一群人跑出来,我婆婆手里拄着根拐棍跑在前面: “挨刀的呀!你作什么孽呀!我说叫你不要上山不要上山,你偏要去。我家也不缺你那两捆茅草,落个丢人现眼!挨刀的!”婆婆急得直跺脚。 “咋个了?阿妈!”我莫名其妙。 “唉哟哟!”婆婆呜呜地哭了起来,“你把我儿子支开去放田水,你倒是跑上山去找别的男人唱调子,戴茶花!还不快把那朵丢人百代的花扯下来!快扯下来呀,挨刀的!”婆婆气得坐在地上大哭。 身边围着一群人,小娃娃、老头子、抱孩子的媳妇、卖油粉的老太婆,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是猜疑,是同情,又像是讥笑。啊!真叫我受不了! 我急得把草垛往地下一摔:“就是天塌下来你也把话说清楚!是哪个短命鬼说了什么闲话?” “你还有理!你还有理!”婆婆两棍子打在我脚杆上。我急了,抓住她的拐棍就往家里拖。 “走!回家讲去!你给我讲个明白!” 一群人跟在后面起哄,拥着喊着进了村。鸡飞狗跳扬起一路黄尘,直拖到雪梨树下我家小院前。 突然,我站住了,他,我的丈夫,正在台阶上修锄头柄,见我们闹进院来,“当啷”一声扔下锄头,拍拍手站起来,眼光直射在我的脸上。那眼光混合着恼怒、爱怜和一些复杂的东西。我从来没见过他的表情如此难看,心怦怦地跳了起来,“天哪,今天不知要出什么事情。” “阿妈你莫急,你叫她自己讲嘛!”他把婆婆拉到一边。 “讲什么呀!那朵花……那朵头上的花!你快给我把它扯下来!天老爷爷!”婆婆气得声嘶力竭,一脚踢开旁边的一个猪食盆,汤水流了一院,七八只小猪从马房的草堆里乱跑出来,吱吱地叫着舔吃。 “花咋个了?花是阿秀嫂给我的,惹着哪个天王地老子了!”我一把扯下那朵蔫了的花扔在婆婆面前。 “花……花是山箐里砍树人给的么?你说呀!说清楚了我放狗咬死那个短命的砍树人,跟你没关系!”婆婆抹了一把泪,站起来朝我说。 “什么砍树人?谁说的?” “唉!背茅草的巴巴鱼她们都看见了,村前村后都在讲呢!”婆婆又呜呜地哭起来。 一股仇恨从我心里升起,那张扁平脸和那张嚼着一片树叶子的瘪嘴又在我眼前晃动,“巴巴鱼!我今天非跟你讲个清楚!”我转身进马厩里,拉出一根套马的皮绳。 “你要干什么?”丈夫一把拉住我的手。 “找她讲理去!”我的眼睛狠狠盯着一个地方。 “莫瞎闹了,她有她的坏处,但你那个脾气也要改改了!” 听见这话,我眼泪一下涌出眼眶。但我咬住嘴唇不叫自己哭出声来,甩开他的手冲出院门。 一群看热闹的人正贴在墙根角听巴巴鱼讲什么。她懒洋洋地靠在那里,左边嘴角衔着一根麦秆,右边嘴角在飞快地说,手里编着草帽带。一看见我,她话音止住了,眼珠子动了动,眼皮斜塌下来,嘴角上故意露出一丝轻蔑的笑。 “巴巴鱼!你到我家说什么了?” “说什么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嘿嘿……” 我拨开人群,一个耳光打在她那张扁脸上。 她一惊,嘴张得老大,突然大叫:“烂货!你敢打我!今天叫你看看老娘也是本主养的!”说着就扑了过来。 我顺势一偏脚把她绊倒在地,扑上去把她死按在地上。人群喊叫起来,我婆婆拐棍戳在我的脊背上。 “挨刀的,你莫把人捶死了!起来,起来,我给你跪下!”婆婆在喊。 听见婆婆喊,我更是火冒三丈,一跃身骑在巴巴鱼背上,揪起她一撮头发: “巴巴鱼,你说!你还敢不敢造谣糟蹋人!” “哎哟!我死了!今天我是死定了!死定了!”她鼻涕口水地爬在地上乱嚷。 “你说不说!”我又使劲地在她身上扭,搓得她肚皮在地上蹭得生痛。她又哭又叫。 “莫打了,莫打了!自己规矩点就不惹事了嘛,打有什么用哇!”人群中几个老太婆在喊。 “嗨!自己要戴花,又听不得别人说,自找麻烦!” “哼!哪家的是非不是她搅出来的,打!打死喂狗!”阿秀嫂在人群中挤出一个头在朝我喊。 “不会生娃娃,就会生是非!”几个女人也在喊。 突然一只有力的手狠狠地把我从地上拖起来,拽着就往家里走。他,气冲冲地把我甩在一张椅子上,砰地关上门,双手抱在胸前斜靠在门上,脑袋后就是那个几天前我们一起剪贴在门上的大红喜字。 “你……”他气得话都说不出来。 “我……”我大哭起来,跑过去使劲地捶打着他的肩膀,心里的委屈、恼怒一刹间化作淋淋的泪雨。 “好了!莫哭了,呵……听我的话,以后改改你那个又爱美又要强的脾气,呵?我们都有家了。你说,你改吗?”他用双手轻轻撑起我泪涟涟的脸。 “不……”我仍旧不服气地摇摇头。 他猛地一下把我推开,气哼哼地说:“那……那你这样下去叫我在村里咋个做人?你倒是有趣,今天戴朵花,明天插根草,不知要给我惹多少喳筋事!” 我突然觉得站在我面前的他,有一种特别叫人可怜的东西,就好像刚才那一场风波是他闹起,我为了戴一朵花引来的灾难,全部降落在我面前这个人身上一样。过去我常常戴花,他也爱我戴花的模样。今天我戴一朵花,就让巴巴鱼大闹一场。难道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不一样了吗?这时我突然觉得在他靠着的那扇贴红喜字的门后,又一扇看不见的门打开了,一片灰蒙蒙的迷雾从另外一个世界飘进了我的心房,使我感到一种朦胧的压抑和隐隐的恐惧。我好像突然间理解了村里那些媳妇为什么总是悄悄地打扮自己,打扮了又怕别人看出来的原由。我又想起了有一次从城里带回的那块粉红色的纱巾,在阿秀嫂心里引起的那种欣喜又忧怨的感情:“我戴它?莫叫别人笑死……”现在我才明白,“叫别人笑死”并不是无所谓的事,它会给我心上,给我亲人心上带来沉重的痛苦。这一切都是巴巴鱼一个人造成的吗?不!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比巴巴鱼更强大、更能束缚人的模糊的东西,从那扇刚刚打开的门里涌了出来…… 走到什么地方了?突然意识到沉重的草垛还压在我的肩上!我抬起头来一望,只见那峻峭而美丽的山峰插向碧蓝的天空,而在这些卑视一切的巨人般的山峰峭壁上,开着一蓬蓬嫣红的山茶花。不知是走得太累还是这景象太玄乎,突然间山峰、蓝天、峭壁上的花都旋转起来…… “啊!该不是做梦吧!”我好像刚刚从一场纷乱的梦中醒来一样,胸前一阵隐痛,肋骨被绳子勒得难受。解开绳子,待背上的草垛滑落在地上,我顺势向后一倒,靠坐在草垛上。安静极了,不远的树林后面,一道清澈的山溪从岩石上跌宕下来。我急忙跑过去,伏在石头上喝了个够,顿时觉得清爽了许多。唉!我闹了什么事了?做新娘……戴花……打闹,唉!我真不该去闹那一场是非,也不该把巴巴鱼往死里捶打,也许她今天还睡在床上哼哼呢,早起也没见她来割草。我不该打她呀!人世间的有些事情确实说不清楚。我不该怨她,该怨我自己,怨自己为什么没有意识到从做新娘的那一天起,人世就已经悄悄地变了! 我坐在溪边石上发呆。静静流淌的水面上,有粉红的花影?低头一找,才发现我坐的石头边上开着一株山茶花。我顺手摘了两朵。突然,我仿佛又看见婆婆哭闹着举着拐棍从村里跑出来;仿佛又看见我丈夫那炽热、恼怒又充满爱怜的眼光,和从那扇贴着红喜字的门后飘进来的那层灰蒙蒙的使人压抑、恐惧的雾;看见那些起哄的人群和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各种各样的眼光,带着善良与苛刻、良知与愚昧、赞许和轻蔑,把我天生的那种喜好美的性格淹没掉,而剩下的只是一个连一朵花也不敢戴的小媳妇,孤独地坐在这深山溪边悄悄地想着自己的心事…… 清亮亮的溪水里飘着一点点粉红的花瓣。一点点,粉红的,像泪。谁哭了?我望着手中撕碎的茶花,心里一半是怨,一半是恼:“谁让你开的呀,你这不懂人间事理的茶花!满世界都是寒风、冷雪,谁听说过十二月还开花?你不开,我就不会想起要戴,就不会惹事。就是你!就是你!”我又狠狠地撕碎两片花瓣扔进水里。当我抬起头来,只见那一蓬蓬山茶花开在绝崖峭壁上,开遍山箐丛林间,光彩夺目,火一般的强烈,火一般的红!啊!我又仿佛看见了一个鲜亮的世界,一种崭新的生活。多好的世界,多好的山水和泥土啊!就是在白雪覆盖的冬月间也忘不了生发出一派艳丽的花色,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雪山浮在茫茫的云海上,仿佛要随着缓缓移动的云朵一起飘去,不知要飘向哪里……也去做新娘吗?像我一样……头上戴一朵茶花?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逢入京使》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安徽省
- 化学九年级下册全册同步 人教版 第22集 酸和碱的中和反应(一)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老山界》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安徽省
- 苏科版数学八年级下册9.2《中心对称和中心对称图形》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泊秦淮》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天津市
- 苏教版二年级下册数学《认识东、南、西、北》
- 冀教版小学英语五年级下册lesson2教学视频(2)
- 19 爱护鸟类_第一课时(二等奖)(桂美版二年级下册)_T3763925
- 苏科版八年级数学下册7.2《统计图的选用》
- 沪教版牛津小学英语(深圳用) 四年级下册 Unit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