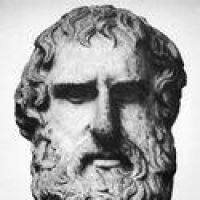海涛
/文学
远山
作者:海涛 海练[仫佬族]
飘忽不定的浮云,像肮脏的擦布一样,阴沉沉地缀在苍穹之下。风,一丝也没有。缓缓落向森林、大山的寒雾却愈来愈重。不一会儿,蒙蒙的细雨飘飘拂拂地下起来了。 雷雄弯着的腰直起来,抖抖发麻的双手,瞟了一眼还埋头在水里淘样、双手被冻得紫红的耿成明,什么也没说,走上岸,把铲子往岸上一丢,哆哆嗦嗦地跑到篝火边。
陈年的腐叶在他脚下沙沙地响。 雷雄头发蓬乱,雄健的身躯像巨蟒一样蜷缩在那里。他身上只穿着毛背心和弹力裤叉,熊熊燃烧的篝火,张牙舞爪的火舌,不时映照着他裸露着的、紫红的手臂和粗壮的双腿。他似乎完全失去了知觉,眼睛看着不远处的山谷,一动不动。 这是一条阴深幽暗的山谷。
谷底嵌着一条沟水,沟水最深也不过齐腰,水面约两米余宽,两旁矗立着犬牙交错、垂满道道藤蔓的、让人目眩心惊的绝壁,一座座面目狰狞的大山,像大海掀起的狂涛,铺到天边。山上自然生长着千姿百态、粗大而古老的樟树、楠树、杉树……古木阴森,遮天蔽日。抬头望,无垠的天空被割得只露出斑斑驳驳的碎块儿了,谷里满是浓雾,想看深些,就是迷迷蒙蒙的一片,无法辨别深处的虚实究竟,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水面仿佛是凝固了似的,长年累月凋落的树叶,一层又一层,几乎看不见水的影子。一种难闻的霉味的昆虫的腥味,弥漫在空中。
一股又辣又呛的青烟,飘到雷雄的脸上,他抬了抬粗眉,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忙把被火烘烤着的双手抽回来,又瞄了一眼站在水边的耿成明,似乎感到自己应该去帮他一把。但是,身子还没站起来,那股莫名其妙的怨气却又上来了。他想:要不是这不通情理的小老头,他死活也不会在这荒野受罪…… 一年前的一个深秋的黄昏。殷红的夕阳把辉煌的霞光温柔地洒在十万大山茫茫的原始森林上。 大山,穿过一片片密林。
就凭这个准行。 但是,雷雄失望了,耿成明听罢他的诉说,竟变了脸,眼一瞪,劈胸就给了他一拳:“窝囊废,有这个必要吗?以往的话都白说了,这一切算得了什么,真正地质郎的儿子该是怎样,你不懂?领导同志们又不是吃素的,气个球……”就这样,刚开春,雷雄怏怏地跟着他闯入了这座全封闭的原始森林…… 现在,雷雄望着那幽深恐怖的山谷,看了眼躺在脚下的一小捆皱巴巴的样袋,心里的那种从来没有过的情绪又在折磨他了。他不由沉重地叹了口气。时间过得真快,再有十天就是散布在这方圆百里的各小组在松村林汇合的日期了,可什么时候才能淘洗完呢?妈的,熬吧,熬吧!就让他们多说几天。 起风了,天气变得越发阴冷了,绵绵的细雨越来越厚,像霰雪一样洒在他俩温暖的肌肤上。
苍苍莽莽的群山,也变得越发模糊昏暗。 “够了,快下来吧!”耿成明看也没看他,冷冷地说了一句。 雷雄提起铲了走进水去。顿时,仿佛凝固了的水浮动起来。树叶纷纷闪开,像撕裂了个口子,但很快,那些树叶、水藻又毫无顾忌地聚扰起来。
紧接着,沙虫开始作怪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奇痒刷地传遍全身。他万想不到刚一会儿的工夫,这水竟像冰冻过一样。他不由得打了几个冷颤,浑身起鸡皮疙瘩,像被什么东西咬着似的。他扭动着舞起铲子,往盆中铲着沉积沙呢。 这区域是属于古生代寒武系地层,由于造山运动的影响和种种地质应力的作用,形成山势峻陡,切割成大起大落的地势。
山头、山脉全被第四系浮土和怪木莽苍的植物所覆盖,只有在深深的山谷里,才有清一色的灰绿砂岩出露。因此,雷雄一连几铲下去全碰到铁硬的岩石,手震得生疼。没一会儿,彻骨的寒意迅速扩展到他全身,奇痒感觉消失了,手脚开始渐渐麻木了。“妈的,这里沉积物也太少了!”他愤愤地骂了几句。 “淘样不能单凭力气!”耿成明似乎故意挖苦地说。
雷雄抬起头,想说什么,见他跟前的陶沙盆里的沙泥(注:每个样需要用30公斤的沙泥,而30公斤的沙泥,又要分成两次淘洗出70-100克左右的重沙泥为止。)还不到六公斤呢!他忿忿地低下了头,心里陡地升起股气,一种强烈的报复欲望充满胸间。他不愿看到耿成明那轻蔑的样子,心里恨不能就在几天之间把这条山谷淘洗完,马上出山去。他咬着牙,憋着气,挥动着铲子,把水弄得哗哗地响,然而这毕竟是憋着气,他冻僵的四肢并不听从大脑的指挥。他似乎感到这寒冷就像无形的针,已扎进了他的心脏,一铲又一铲都落空了。
“上去吧!”不知什么时候,耿成明来到他身旁。雷雄机械地把铲子给了他,摇摇晃晃地拖着沉重的步子,奔命样地赶到篝火旁。 加了把干树枝,跳跃的火焰一下窜得好高,雷雄几乎有些神经质地在红色的火舌中蹦来跳去,任凭火舌咬着他僵硬的四肢,直到感觉有些火辣辣的时候,紧张的神经才松弛下来。 耿成明哆哆嗦嗦地上来了,他嘴唇发麻,身上皮肤冻成紫酱色,什么也不顾,迫不急待地掏出那壶酒,仰着脖子不知呷了多少口,才拉风箱似地喘起粗气来。 “这哪有点春天的味呀!简直比寒冬还冷。
”耿成明喷着酒气嘀咕着走过去:“嗳,我说雷雄呀!你不来一口吗?” 他装着没听见,背过身去。雷雄不想理他。 雷雄和他的一位好朋友往宿营地走去,途中,遇到了滚滚翻腾的泥石流。过后,雷雄在泥石流上游基岩中,发现了一块完整的鱼化石…… “老兄!你睁大眼看看!”晚上露宿时,雷雄借着闪烁的篝火兴奋的端详着放大镜下的鱼化石说:“这是块非常有鉴定价值的化石!” “是呵……老弟,你这次可走运了,我们师傅爬了半辈子山,也没碰上……来,恭贺老弟,咱们干它一杯……” 雷雄心花怒放、开怀畅饮,几搪瓷碗的烈酒下肚,醉了…… 清晨,雷雄醒来,昏昏沉沉的,头好痛。他从地质袋里掏出那块化石。
怎么?变成了普通的石头。他惊愕地连连在心里发问:是我昨晚花了眼么?是我做梦吗?……他不解、惶惑,揉揉惺松的睡眼,再看:不错,手里的的确确拿着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忽然,他望了一眼甜睡的好朋友,似乎想起什么,笑了。 “哎!别装了,把化石拿出来。”雷雄推醒了他。
“什么化石?” “嗳,就是昨天傍晚我捡到的那块鱼化石呀!” “噫!我说你小子别是灌昏了头吧!谁见过你什么猫化石、鱼化石的……” 就这样,雷雄怀着疑惑的心情回来了。但是,没想到,这位好朋友一年后从野外回来,却拿着那块鱼化石报功去了。他一眼就认出来了,告了那家伙…… 可过了几天,雷雄发现事情愈来愈严重了,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有那么些异样得让他感到冷峻、尖刻、刺到心里去的目光跟着他。甚至还听到了挖苦声、骂声: “哼!想不到他什么也没学到,嫉妒却学到家了。” “妈的!这些年轻人也不知从哪儿学的,真没法。
” …… 雷雄气得两眼直冒火,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这样看。他彻夜失眠,无度纵酒,窝着一肚子的委屈、怨恨,四处寻找那无耻的剽窃者,非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就在这时,地质矿产部下了指示,要组织技术人员对那块由于受到种种客观条件限制,在祖国地质矿产图上还是个空白的全封闭的原始森林——一块未开垦的地质处女地,进行调查。这天,召开了动员报名大会。雷雄人虽坐在那里,可心却一直在如何尽快弄清楚那件事的真相上,所以,当十六个自愿报告的筛子一轮,只选了九个富有经验、身强力壮的留下,而最后还差一名时,刚从部里回来,负责这次调查的耿成明喊了起来:“雷雄,雷雄来了没有?” “呵,在这儿呢!” “你小子带耳朵来没有,一百四十斤是留着吃干饭的吗?……把他名字记上。
” 雷雄望着他,眼一亮,流露出无限的喜悦来。他想说不去,可嘴巴阖动了半天,还是没说出来,似乎觉得现在不是时候。 散会后,他去找耿成明。路上,雷雄想:好了,要把自己一腔的委屈、怨气都告诉他,别人不敢说,耿师傅自然会理解自己,他会让我留下的。这不仅因为他是这次调查的领队,同时还是父亲的师傅和媒人呢。
后来考上地质学校时,自己装衣服的箱子还是他连夜给赶出来的。每次进山,只要他在,总少不了叫自己去喝两盅,唠叨他以往出野外的经验。雷雄敬佩他,这不仅因为他曾发表过铌、钽稀有元素矿床方面的独到论著,立下大功,而且雷雄惊奇地发现,在他身上似乎有股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能使自己信心倍增地翻过一座座高山。 是的!雷雄觉得他太不了解自己了……这一切算得了什么,亏你还是地质郎的儿子呢!……雷雄永远也忘不了他说话时那副轻蔑的样子,叫人什么时候想起都来火,哼!漂亮话谁不会捡起卖。他想:若这事轮到你耿成明头上,我敢说,你不气得蹦到屋梁去才怪哩! 耿成明不管他理不理,自个儿炫耀着:“唉!酒可是最好的东西,有了它!不怕风,不怕雨,不怕老婆发脾气……” 雷雄扭过头不满地翻他一眼,似乎在说:“喝,喝,你不知道就是他妈这倒霉的酒害得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么……”他觉得这简直是在有意刺他。
他愈想愈气,起身走到水边一块突兀的石头上。 被搅动的水恢复了平静,许是雾重了,雨密了,阴森森的山谷,越发显得迷蒙、恐怖而昏暗。他伫立着,感到心里的忧闷、压抑愈来愈重。凶猛咆哮的江河他畅游过,大海的狂涛他搏击过,然而现在却被这条又小又浅的水,一次次逼上岸去。他感到脚肚有些瘙痒,是什么?低头看时,是好几只山蚂蟥爬在上面。
两只许是吸饱了,舒舒适适地躺在脚下。“去你妈的!”他狠狠地捏着几个摔到岩石上去。此刻,他似乎觉得浑身都不自在了,无论是这小小的蚂蟥,还是这水,都像那烦人的往事一样,在欺负他、愚弄他、嘲笑他,跟他过不去。于是,雷雄晶黑的眼睛迸射出怒火。他发疯似地操起铲子,冲入水中,不顾脚下刀锋箭簇般的岩石,不顾难忍的瘙痒,不顾刺骨的寒冷,骂着、铲着、嚎叫着,那歇斯底里的声音,仿佛肺腑已撕烂似的沉重、压抑,在死一般寂静的山谷里,久久地撞荡着、震撼着。
耿成明忙跑下水,连吼带拉地把他推到火边:“你小子疯啦!坐下,瞧你那样,整天就懂憋着股气,心眼干嘛那么小……” 雷雄没出声,抱着头,十指紧紧揪住头发,仿佛要把什么都发泄在这上面…… 傍晚,他俩返回驻地。 这是一个好地方,真的,只要利用那些粗藤攀上去即可避雨,又可以躲过野兽的袭击。恐怕哪儿也找不着了:在陡峭的绝壁上,凹着一个穴洞,四周悬吊着盘根错节的长青藤。峭壁下,爬着厚厚一层绿苔和蕨叶。一脉潺潺的溪涧,就从灌木丛生的山脊淌泻下来。
朦朦胧胧的暮色暗暗地从远山伸展了过来,苍穹和群山融为幽邃的一体。天色骤然暗了许多。 雷雄升起篝火,周围的一切似乎都颤动、摇晃起来,猖狂的火舌围住吊着的水壶咬着、舔着。 他脱下翻毛皮鞋,烘烤潮湿的袜子,不时皱起眉头,侧身躲过蒸腾上来的那股怪味,这样,燃烧的湿树枝“噼啪”溅起的火星,往往会在尼龙袜上留下一个个小洞。每次,他都像端详什么有趣的东西似的,默默数着:“一个、两个、三个……”仿佛这是种极大的乐趣。
然而,没多久,他又觉得没意思了,扭头想跟荒野中唯一会说话的人聊聊天。 耿成明这会正趴在穴洞边,用条长茅草叶从峭壁上引着涧水,灌入壶去。他似乎很高兴,嘴里五音不全地哼着:“克拉玛依,我不愿走近你,你没有人烟,没有歌声……” 但是,雷雄喉头上下滑动了几下,也没说出句话来。他把目光移向黑黢黢的夜空。肃穆、神秘而博大的森林里,不时断断续续传来一两声猴子的叫声。
不知为什么,现在,一见耿成明那样乐他就心烦,就自然会想起那事,想起那个灵魂肮脏的小人来,想起自己的委屈、怨恨和痛苦。有时,想得几乎受不住了,他干脆闭上眼睛,以极大的克制力压抑内心的寂寞,试图尽量聚起精神想那些最感惬意的事——儿时放风筝,他系着鸽哨的风筝总比别人的高一截……那角球发得可真是绝了,直接发进大门……中国女排获得世界冠军,刚发的薪水全买了鞭炮……但是,这一切努力几乎都是无用的,这种烦躁和委屈,不仅盘绕在他整个脑袋,而且似乎很快就会把脑袋胀爆了。 水开了,他俩默默地嚼完粘乎乎的压缩饼干,胡乱淋了下脚,一个头朝东,一个头朝西地钻进被子。 从进山分组那天起,他俩天天都这样,除了工作上说上三两句话外,几乎全是在沉默中度过的。开始,耿成明还嘻嘻哈哈无话找话和他聊两句,但碰了几次钉子后,似乎也懒得理他了。
只好一个人自得其乐地品起酒来,嘴里还不时哼起那支老掉牙的曲子,眼睛却乐乐有趣地看着那些硕大的黑蚂蚁偷袭着因吃得太饱而从树叶上掉下的昆虫,偶尔也捉起一两只蛤蟆玩玩、看看,唠叨着:谁说蛤蟆没有毛…… 这不是有意气我吧!雷雄则常这样想。 第二天清晨,雷雄醒来,天已大亮了。他觉得头很重,疲惫的四肢软绵绵的,整个身体似乎有片浮云托着。他挣扎着想坐起来。 “别动。
”耿成明叫住了他。 雷雄睁着惺忪的睡眼,望着他挺纳闷:我这是怎么啦?他似乎记得昨晚回来,觉得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手脚沉重,冰凉冰凉的。于是,吃了点馒头和几块压缩饼干,就钻进被子。他疑疑惑惑地自语:“我这是怎么啦!” “还怎么啦!你小子睡觉一点不老实。瞧,着凉了吧……来,喝碗热汤驱驱寒!” “哟,蛋汤。
”他心头一阵惊喜,咕噜噜喝起来,不知多少天了,大便都不通畅。 “哪来的!”雷雄问。 “这还用问,靠山吃山咧!树上掏的。” 耿成明嘴上尽管说得很轻松,眼里却流露出一种不易察觉的忧郁、担心。是的,他心里十分清楚,集合的日子快到了,可“样”只淘洗了还不到百分之四十呢。
雷雄进山前打过预防针没有?记得那天他好像漏打了。但是,他没敢问,怕他如果真没打,知道病情岂不更增添精神负担么?万一挺不过,一切都难以想象了…… 肚子热了,雷雄觉得舒服了许多。他起身说:“该走了吧?” “别起来!”耿成明忙把他压住:“这几天够累的了,今天休息一天吧!” 雷雄脸色变了,皱起眉头:嘲笑我吗?没门。他鼻子“哼”了声,猛掀开被子。 “雷雄!” 这时,他听到一声严厉的、既陌生又熟悉的声音。
他扭过头,怔住了。他没料想耿成明的脸色绷紧得那么吓人,目光坦率而严肃、而严肃之中还混合着一种关切和疼爱。 “听好!”耿成明说,“我要你今天给我好好躺着……你病了,药就在枕边,马上吃。” 雷雄完全被他的威严的力量慑服,几乎是机械地点头默应了。 他吃过药,耿成明嘱咐了几句,说“我出去一趟,一个小时左右就回来……” 耿成明走了,他侧过身子,直望到那瘦小的身影和黛蓝色的大山、森林融为一体。
天气还是很糟,??鞯南赣晗裼涝兑渤恫欢系乃肯撸?唤舨宦?仄?髯拧N淼?诵??诿苊芙恢?氖髁旨溆我谱拧⒘鞫?拧E既灰徽笊椒绻卫矗?啪驳纳?窒炱鹨徽蠛涿??韧蝗缙淅矗?址浅V?嫣亍?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