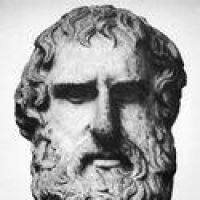黄薇
/文学
流浪的日子
作者:黄薇[蒙古族]
一 我是在暮春一个杏花开得正旺的日子里认识他的。 那时我去找措姆,经过传达室,他就站在传达室开着的窗里。当时天开始出现暮色,但仍很蓝很亮。所以能看见传达室屋里脏兮兮的灰墙壁。敞开的窗户框和玻璃也很脏,灰扑扑的。他在窗户里笑,有烟垢的牙齿很长很灰,脸也很长,呈现出一种胃不好的灰色。他当时给我的印象仿佛一张镶在灰镜框里的旧照片。 他不知正和屋里的人说什么,很投入的样子。但我想他应该是注意到我了,他的眼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钟,然后掠过,他笑了笑,我拿不准这是否是冲我笑的。我从传达室前走过去,我很想回头,但还是克制住了这个欲望。他的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落寞而又悱恻。当然这会儿我还不知道他是谁。 我觉得这不能说是爱,一见钟情是一些小说里被用滥的情节。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我也说不清楚了。是否是因为措姆总是对我讲起他,而人为造成一种强行灌输的效果?这么想又让我觉得自己很卑鄙。所以我后来常常思忖这个问题,以期反思自己。但也许是我对这个问题反复进行思考,而经过了无数思考便拉长了时间上的感觉,以至这个问题竟变得不可思议,就像幼年曾经历的某件事,由于年代的久远而让人怀疑是否有过这件事一样。到后来,我已恍然觉得措姆不过是我和他的故事的听众,是我在敷演自己的这出戏。他死后,措姆问,谁与他的关系近?我就觉得她简直滑稽透顶。 我从传达室前走过,走进措姆家,发现她买了新家具和双人床。我惊讶地问,打算结婚吗?她闪闪烁烁地说,结过了。我觉得这就跟变魔术似的,你已经结过婚了?什么时候?措姆支吾道,早的事了。我说,早的事也是结婚了,你怎么从没跟我说起过?措姆看了我一眼,你把这个看得很重吗?我当时以为措姆指的是没告诉我已结婚这件事,后来我才想她其实说的可能是“结婚”本身。我有点不高兴,当然,这是信任问题。停了一会儿,措姆忽然说,我讨厌说结婚这事。我还没出生,家里就把我嫁给了那家伙,能想象吗?今天还有指腹为婚! 我说不清她脸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神色,她的眼光在那一刻变得干燥粗糙,像张沙纸一样打磨着我的脸。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措姆在此时就预见到后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已经走进命运为我安排的阴谋和圈套中了。 我躲开她意味深长的凝视,目光像鱼似的在她脸的周围游了一圈,然后滑过去停在桌上摆的一张相片上。那是两年前我们俩在青海的塔尔寺照的。那年我们休假去了塔尔寺。相片上我们站在小塔前,身后是一条翻浆的泥泞土路,上面清晰可辨一道道的车辙。 就这时,措姆的丈夫走进来,原来就是传达室里的旧照片。他叫桑杰。于是,在我的记忆中,桑杰就是沿着那些纵横交错的辙印走进我的生活的。 桑杰朝我点点头,就把眼睛挪到措姆脸上,后来就没有和我的眼睛接触过。他问措姆,这就是你的朋友?措姆说,朋友。过了一会儿,桑杰就用蒙话对措姆说起来,措姆微微笑着不说话。他俩紧挨着一起坐,措姆的手放在他的手里,看上去非常亲昵。我下意识地想,措姆永远都是这样口是心非,她的话永远不能知道哪句真哪句假。 那晚他们留我吃饭,饭很简单,但酒很多。桑杰很能喝,他把一盅白酒倒进一玻璃杯的啤酒里,这叫作“一挂”,他一共喝了十七挂。这十七挂酒染白了他的脸,在我也因喝酒而变得飘忽和迷离的眼睛里,桑杰那张长脸仿佛一张画上了人的五官的白纸,那张白纸。寂寞无声却又万分悲凉地晃荡出投降的信号。桑杰喝了酒,就更多地用蒙语讲话,措姆有时会笑,有时就看我,像毛刷一样在我身上这儿刷一下那儿刷一下。 我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措姆送我到门口,我说别送了,就把她推回去。替她关上门。门夹住了桑杰的声音,他在唱歌,正唱着“岸边的骏马拖着缰”。这是一个关于女人远嫁他乡的古老的蒙古民歌。 门洞里没有灯,楼前的甬上也没有灯。只有每家窗户射出的光在地上照出半明半昧的光影。我站在屋里灯光之外的黑暗中。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向楼门外走,这声音一点点淡下去,很快就消失在嘈杂的街声里。我一直觉得这一夜有种凄凉和感伤的味道。 二 我不记得桑杰活着时,我是否就认识了孙敬。这很古怪。我问过措姆,她睁大眼睛惊奇地说,你怎么了?我不知道我怎么了竟值得她这么问我,只是她到底也没回答我的问题,所以这一直是件奇怪的事。 我很难清晰地描述孙敬。他是大夫,还是男人。不漂亮也不难看,或者说有时候看上去好看,有时候则很丑。他缺乏激情缺乏幽默感,看任何人任何事都很理智客观,差不多像在看一个扁平疣,一块牛皮癣或者一片红斑狼疮,总之是一种非常职业化的态度。 那是个周末,我们坐在他那很干净的屋子里。他身上有很浓的来苏水的味道,这股味很快就弥散到整个房间。我摸着他的手,那手很小,手指很长,非常像女人的手。那双手冰凉。我下意识地想到帕瓦罗蒂唱过这样一双“冰凉的小手”,这当然风马牛不相及。我轻轻搔着他的手心,又轻轻向前摩挲手指,我问,你的手为什么老这么凉?没什么病吧?他挣开我的手,好像那是个束缚。我觉得,他不喜欢柔情,我向他抱怨说和他恋爱是很苦的事,因为他不过把我看成一个肿瘤之类。他很正经地说,你错了,我不会这样看你,我不是外科大夫,是精神科大夫。 他推开我的手,好像推开一个束缚。他说,没事。就走到晾台上。他住在十六层楼上,从十六层楼上往下看让人眩目。他看了一会儿楼下像是缩微了似的建筑、树木和人,就转过身,靠在门框上,像百无聊赖般看自己那双女人一样细长的手指,平平淡淡地说,说到病嘛,谁都多少有点,比如桑杰就有妄想症。 我愣了。 我和孙敬是在火车上认识的,我去开一个什么会。那次我选择了一条要经过草原的路线。过了一个叫土牧尔台的小站,火车就进入了草原。铁道从草原中间穿过,像用犁犁出了一道壕。放眼望去,极目所至一片无尽的绿,没有人没有树没有房,天地浑然一体。后来渐渐地看见了羊群,像飘曳的白云,从空旷、辽远的浩瀚中缱绻地飘来。我被一种说不清楚的温柔弄得心里酸酸的,我看见桑杰扬着他那张长脸,朝天边的太阳跑去。这时桑杰是否已经死了,我不记得。我不想推算这个时间差,时间并无意义,问题是他反正是在我们都活着时不在这个世界上的。 这时,孙敬应该就坐在我附近,不过我没有注意。直到夜里。夜里我被人推醒了,那人站在我卧铺前的走道里,你作梦了。他就是孙敬,只是那会儿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很狼狈,低声说,真不好意思。他也低声说,梦见桑杰了,他对你很重要,是吧?当时我也是愣住了,也许是我说梦话叫了桑杰的名字?我不知道。 我怔怔地盯着他。车厢里早熄了灯,人们都睡了,一片鼾声,只有小桌底下还亮着瓦数很小的灯。朦胧中,他脸上掩了些昏暗,但还能看清他,不漂亮也不难看,头发显得有点稀疏。然后,我一言不发地重新躺下,面对着卧铺的隔板,我哭了。 这是一个冗长的无眠的夜。 后来我对他讲了桑杰。在静寂的椴树林中,林间小道上散落着秋天蜕变的蝉壳,金黄的秋色透过树梢,酒在五彩缤纷的野花上,桑杰背着空空的行囊,低着头慢慢踯躅在小路上,好像在搜索什么遗失掉的东西。他仿佛一个久别重归的浪子,一个疲惫不堪的跋涉者,他的困顿引起了我无限的爱意和柔情。孙敬一直看着窗外。 正是中午,外面一定很热,草地上氤氲着一层烟似的雾气。我清楚地看见桑杰从草地深处走来,在飘荡的雾气中,他的身体像做柔软体操似的来回扭动。我疑惑地看看孙敬,发现孙敬脸上的表情很古怪,他的脸先是发红,然后变得煞白,眼睛里还像有了泪那样的闪光,那一刹那,他的面孔变得柔和起来。我不知道他怎么了,是因为桑杰还是为了窗外的草原,但肯定有什么让他受了感动。就为了这个,我和他后来才有了来往。 可现在他却说桑杰有妄想症。 我盘腿坐在沙发上,仇恨地瞪着他,你瞎说。他抬起头,用两根手指弹着窗玻璃,很随便的样子说,应该是你不能瞎说,那个关于浪子,关于跋涉者的故事是假的,你知道椴树是什么样吗?桑杰甚至连蝉蜕这个词都没听说过。这个故事是谁编的,你?桑杰?大概是桑杰吧,你应该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讲出来。 我忽然泄了气。桑杰那张寂寞的脸在我面前栩栩如生地苦笑着。我凄惶地看着孙敬,他身后是九月血一样殷红的薄暮。 三 我一直认为措姆和桑杰的关系很好。 桑杰经常用呜里呜噜的蒙语和措姆说什么,措姆听了就笑。我说你们这俩家伙连礼貌都不懂,故意让我难堪。措姆说,他说的是情话,你想听吗?他俩也总是依偎在一起,桑杰用一只胳膊绕了措姆的肩,他们的手也一直是交叉着。这很像表演,但我承认我嫉妒措姆。 后来有一天他们吵架了,我才恍然意识到他们之间是多么互相仇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吵,也听不懂他们的蒙话,但看上去他们非常激动,措姆恶狠狠地不断朝桑杰叫:“依勒根那!”桑杰显然说不过措姆,他铁青着那张长脸,不停地用手拍桌子。大概是忍无可忍了,他忽然大叫一声“依勒根那!”,就冲过去用手卡住措姆的脖子,措姆用脚使劲踢他。我生气了,跑过去用力掰桑杰的手,我冲着他的脸吼,“依勒根那!”又转过头对措姆吼,你也是“依勒根那!”我当时以为这是个骂人的话,大约是混蛋、王八蛋一类。 他俩受了惊吓一般忽然同时噤住声,桑杰松开手,怔怔地瞅着我,措姆则把脸扭开。桑杰想说什么似的张了张口,欲言又止,接着推开门走了。 我不知为什么觉得自己很累,我坐在沙发上,颓然地说,为什么吵架,你们不是很好吗?措姆还站在原地没动,她朝着窗外,眼睛不看着我,所问非所答地说,你知道什么是“依勒根那”吗?“依勒根那”是“汉人!”我吃了一惊,这是什么意思? 措姆走到窗前,额角抵在窗户上面说,桑杰这个人呐,她的声音好像患了感冒似的。桑杰和措姆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他小时候很孤僻,话不多,不喜欢和人交往,上学也总孤零零地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有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去草滩捡冬天生火用的牛粪,桑杰和措姆及另一个女孩子在一起,桑杰一直一言不发地跟在两个又跳又蹦的女孩身后。这是唯一的一次措姆用温柔的口吻说起桑杰,整整半天,桑杰什么都没捡,他一个人站在离我们一丈多远的地方玩,玩什么我忘了。然后快傍晚的时候,他从小山坡上跑下去,扬着那张长脸。他沿着草滩上一条人踩出来的小路跑,背上背着用来装牛粪的布口袋,他跑得很快,背上那个长长的打着两块补丁的布袋子就甩起来落下去地拍着他的屁股。多少年过去了,我也老忘不了桑杰的那副样子。那天的晚霞特别灿烂。 这其实就是那个关于椴树林的故事。 四 桑杰和措姆又和好了。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俗语说的两口子打架不记仇?桑杰仍然用嘀里嘟噜的蒙语说我听不懂的情话,措姆也还照旧偎在他肩上撒娇撒痴。谁也不提那天吵架的事,就好像从没有发生过一样。但从那一天起,我们三人关系微妙起来,仿佛在我们之间存在了一个无法言传的禁忌。 很长时间里,这件事都让我觉得恐惧。除了因介入别人隐私而感到的尴尬外,更让我不知所措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个夫妻口角竟会让我有如此噤若寒蝉的感觉。 桑杰常常盯着我看,可当我转过眼睛,他又会马上移开他的目光。我能感到他投在我背上的炽热的双眼。我不相信这是爱情,爱情如果因为看见了一次夫妻吵嘴就产生那也太无聊了。但我承认这双时时处处都能感觉到的眼睛确实让人有种想入非非的激动和亢奋。我很喜欢这种受人注意的感觉。 终于有一个有很浓很浓的秋意的一天里,桑杰来找我,这是他第一次到我住的地方来。他打量我的房间,你很爱干净,挺会收拾房子的。他又用手捻了捻窗帘,这是什么布?多少钱?但他显然对此不感兴趣,这完全是敷衍式的客套。我的身体开始战栗起来,这种战栗像是发烧时的那种畏寒的感觉,指尖和全身的关节处都因冷而发痛。在我和他有数的几次独处中,只有这一次我才是真正地为情欲而战栗,它非常痛苦和可怕。 那是一个秋意很浓的一天,萧条,阴郁,晦暗。飘零的落叶,簌簌的风声,楼房晾台挂着的飞舞的衣物,都让人感到内心说不尽的消极和疲惫。 桑杰坐在我对面,眼光在我脑顶来回游弋。他的口音非常重,完全没有四声的差别,而且字音念得极不准,听上去就跟念错别字差不多。我开始怀疑他会讲情话,即使是用蒙语。 我心里涌起一股潮汐,又很快退下去。这很让人失落。我闭上眼睛,你就是来问窗帘的质料和价格?我可以给你一个价码表。我又感到他烫人的眼光,我睁开眼睛,他还是躲开了。他又朝我脑顶看,那天吵架……我笑笑,对别人家老婆汉子的事我不感兴趣。他说,那好吧。他这话说得很怪,很难说指什么。 他走了,我把他送出去。又跟着他往前走,谁也没说话。后来,他停住脚,你回去吧。他看着我,可眼里空洞无物。我说,那我回去了。往回走了两步,我又转过身叫住他,桑杰,她知道你来我这儿吗?我用“她”称呼措姆,好像我与桑杰之间有阴谋似的。他用语音很不准确的汉话说,知道。我转过身又朝回走,我们中间根本没秘密。 虽然这事不是秘密,但孙敬不应该也不可能知道。因为我认识他时,桑杰已经死了。虽然我始终没有弄清这里的时间问题,不过这不是什么大事。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孙敬却知道这件事,这很让人迷惑。 孙敬问我,桑杰第一次去你那儿,给我讲了关于阴山下敕勒川和土默特部落的历史吧?我矢口否认,根本没有!他问我窗帘什么的。孙敬笑了,会有男人对这些感兴趣吗?说着他拉过窗帘凑在眼前,桑杰也这样看这块布?我瞪着他,我讨厌你!孙敬敛住笑,走过来,可我爱你。他用手摸我的脸颊和脖子,那手凉极了。凉的程度绝不是可以用凉水,冰一类的东西去形容。我后来醒悟只有用黑夜、坟墓、死亡、毁灭、末日等这类词,这类精神和意念中的寒冷才能说明他的手的冰凉。 他盯着我的眼睛说,桑杰告诉你,清初时,敕勒川还是一片牧场。我失控地尖叫起来,不是清初,是明初,你这个笨蛋。孙敬宽容地说,对,是明初,我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孙敬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这点在他的医院里是有口碑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很有节奏地来回晃荡手里的钥匙。钥匙上拴着一根很长的五彩的细绳,绳子很长,长得根本不该用来拴钥匙。孙敬晃着这条拴钥匙的绳子,桑杰是蒙古史研究生,他尤其精通明代蒙古史,所以他给你讲的都是精确无误的,明初那里的草场非常好。“天苍苍,野茫茫”的敕勒歌,连我都会。桑杰用蒙语给你念了它,他念得很悦耳,像唱歌似的,根本不像他说的汉话。可到明中叶,敕勒川那片广袤的草原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板升”。桑杰告诉你,“板升”就是蒙语“房子,村庄”的意思,只是念串了音,就好比说相声的,管“Thank you”念“三块肉”。我说,真恶心。孙敬说,真不好意思,我没有幽默感。 那条细绳继续在我眼前晃荡,先是让我眼晕,后来就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嗜睡感。那条绳子在来回晃荡中不断改变颜色,它勾起了我对某件逝去的往事的回忆。但我不能肯定这件旧事是什么,它也许只是我的某个意念的幻像。
- 二年级下册数学第二课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老山界》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安徽省
- 北师大版数学四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第四节街心广场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逢入京使》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安徽省
- 冀教版英语五年级下册第二课课程解读
- 化学九年级下册全册同步 人教版 第22集 酸和碱的中和反应(一)
- 精品·同步课程 历史 八年级 上册 第15集 近代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
- 冀教版小学英语四年级下册Lesson2授课视频
- 沪教版牛津小学英语(深圳用) 五年级下册 Unit 7
- 苏科版数学八年级下册9.2《中心对称和中心对称图形》
- 沪教版牛津小学英语(深圳用) 五年级下册 Unit 10
- 8 随形想象_第一课时(二等奖)(沪教版二年级上册)_T3786594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其五)》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江苏省
- 二次函数求实际问题中的最值_第一课时(特等奖)(冀教版九年级下册)_T144339
- 小学英语单词
- 苏教版二年级下册数学《认识东、南、西、北》
- 苏科版八年级数学下册7.2《统计图的选用》
- 第8课 对称剪纸_第一课时(二等奖)(沪书画版二年级上册)_T3784187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泊秦淮》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天津市
- 飞翔英语—冀教版(三起)英语三年级下册Lesson 2 Cats and Do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