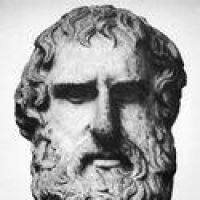黄宗江
/文学
佐临恩师百年写意
作者:黄宗江
人或如树,有其年轮,佐临是我戏剧界一株参天大树,其年轮深厚清晰,刻划着中国话剧百年的迹踪。以“文革”语言发问:“黄佐临何许人也?”答:“戏剧宗庙一大导也!”我是话出有据的。翻旧札,“文革”后佐临赐题我翻译改编剧本《嫁接集》并谑曰:“我不过是个导而已——某国内大官说。”犹忆上海沦陷时期,黄金荣之子黄伟组“荣伟话剧公司”,由属下“大世界”经理兼话剧团经理,盛赞黄导曰:“侬是全国鼎鼎大名的大道具!” 我那时是大导领导下的一名演员,傍依大树盘根错接的一枝小树,然出同根则无疑。我自小在街头看头偶戏,便梦做一流浪艺人,及长拜观杨、余、梅,更长拜读弘一大师、欧阳予倩、洪深、田汉……曹禺霍现,我乃决心进身戏剧殿堂作一艺徒。
量己之才,从演员开始进入剧作。1940年冬我在燕京大学上三年级,因失恋更自愧与抗日脱节,乃别了司徒雷登投身上海话剧界,既演剧又抗日两得了。我投靠的首席师傅、启蒙师尊,梨园界习称奶师,就是佐临。佐临接纳我和宗英还有石挥住在他家,占据了客厅和餐厅,发生了一件真实的笑话:一夜戏罢归来,开冰箱径自取食,随即倒卧。石挥忽呼我:冰箱里的灯好像没关!我三人披衣而起,折腾难眠。
今日思量,一个高贵家庭住进了三名年轻的流浪艺人那是多么费劲费心的事。多少年后,“文革”后某日佐临来北京我家,我不在,我妻若珊接待。佐临提起:“宗江来上海时才19岁,宗英15……”素来寡言少语的恩师,从不抒情更不煽情,却连我们的岁数都记得一清二楚,我能不动情!想到了我们曾戏称他“暖水瓶”外冷内热也。如此恩师我怎么能尽说些冰箱暖瓶大小道具的事,未及他的教诲呢? 我食宿于黄府,可称登堂入室大弟子了。黄不在家,黄太为二小姐喂奶时,我便钻入老师书房,翻阅书橱上层的莎士比亚、肖伯纳、高尔斯华绥等等以至最底层的存档,他在剑桥的硕士论文英文打印原稿《莎士比亚演出简史》,以至对黄太金韵之即丹尼在女中时代上演的莎剧《如愿》的捧角评论。
这样把弟子召家且嘱交约合如今百元的食宿费,其实就是安心费,大概是古有今无的,如苏格拉底门下的柏拉图,孔丘门下的子贡子路等等,他们均记下了老师语录,如柏拉图的《对话录》及孔门弟子记下的《论语》,怎么我没记下黄子语录呢?这也难怪我。佐临密友舞美大家孙浩然被佐临戏称K.P (磕巴)。K.P又还赠P·K(闭口)盖由于佐临从来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尽在不言中了。几十年来我只深记了一则黄门语录,即其长女胖胖(即黄蜀芹,日后一大导)一日在楼梯口自玩橡皮泥之类,其父登楼,忽放一屁,胖胖默默自语道:“爸爸屁股伤风了!”真乃黄门真传,后话无限。 1986年,我应美国国会FULBRGHT基金邀在圣迭戈加里福尼亚大学讲授“中国戏曲戏剧电影”共三学期,讲堂上不得不冲着各色人种学生夸夸“奇谈”。
唬洋人一乐也,当然也得有真的可唬。我必须奢谈从亚里士多德至斯坦尼、王国维至梅兰芳……等等等等。那年正值恩师八十寿辰(如今我也八十五了),我遥奉一贺文亦仅抒情,只有一句理论性或曰学术性的文字:“夫子之道首在于真,方可言善,言美。而求美之道不一,常殊途同归,自诩唯我独真者每失真也。表现变化多端的大千世界的剧场艺术更该是如此吧。
”我此语也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确乎大道求真,然而何为真?历年来说起“真实”、“写实”、“现实”却甚难落于实处,再穿靴戴帽,剪不断理还乱,乃至动辄得咎,甚至得诛。然而到底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艺术的真实呢?中西典籍,浩如烟海,何以拢岸?正此时我获一宝典,即英文版的佐临著《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可真是世界文学艺术比较学的一大巅峰,尤其是一句大白话说到根上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相信第四堵墙,布莱希特要推翻这堵墙,而对于梅兰芳,这堵墙根本就不存在,用不着推翻。”能不为之喝彩!吾师在此文中重申了一次他1962年就提出过的“写意戏剧观”,并英译 “写意”为“ESSENCE”。 对此一英译我就不能同意了,因为“ESSENCE”原意为“本质”,我早就被那类厉声厉色的批判语所吓倒:“难道生活的本质是这样的吗?”我在洋人的课堂上也杜撰了一个英文字眼:“IDEAISM”,此后,在《中国梦》后,1988年在联邦德国汉堡国际东西戏剧交流研讨会上,佐临说:“最近我偶尔碰到一个比较满意的名词,那就是IDEOGRAPHIC与PHOTOGRAPHIC正好相反。
”后者意为“摄像”,前者意为“意像”,这和我当年杜撰的英语IDEA云云近似,我也可以满意了。但是这还没完,就在佐临临终的1994年的春天,他在病榻上对美国归来的外孙郑大圣说:“就像英语里管‘气功’就叫CHIGONG,‘功夫’就叫GONGFU,那‘写意’就叫SHIEYI吧。邓小平说他希望21世纪中叶,外文字典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词,我的愿望是字典里也有这个SHIEYI。” 为了这个:SHIEYI,佐临用了毕生的GONGFU,毕生的CHIGONG。他是个不掉书袋子的真学者,然而他久经实践,博览群书,借助他山之石参透古今中外多少剧内的与诗外的圣贤格言,才逐渐形成了自家的理论。
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他常列案头的如下警句,虽或众所周知,仍宜溯其源流,融汇贯通。语曰—— “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梅兰芳) “不像不成戏,太像不算艺,悟得情与理,是戏又是艺。”(张德成) “虚戈作戏,真假宜人。” “唯绝似又绝不似者,此乃真画。
”(黄宾虹) “这叫既要冲破程式的樊笼,又要受它的规范。”(阿甲) “把一件艺术品分析得七零八落,分解成若干元素,就犹如把一朵紫罗兰扔进坩埚一样荒谬。”(雪莱) “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理想,更典型,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泽东) “情与理,形与神,不可分割。”(马克思) 人世间伟大的发现,科学的,艺术的,或艺术科学的,每每极其复杂累牍繁文难尽,又极其简单可一语以蔽之。
诸如牛顿见苹果落地而获地心吸引论,陈景润一生追索歌德巴赫的1+1。在戏剧理论上,或如布莱希特一崇拜者赞布曰:“你的学说真好,二加二确实等于五。”佐临是不计数码的,却也有个十六字诀:“虚虚实实,实实虚虚,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一语以蔽之曰:“写意戏剧观”。 常言超凡之说之举是空前绝后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佐临的“写意戏剧观”是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有传统有继承有创造有发展,可传世的真经也。佐临不朽!(文汇报2006-09-29)
- 第19课 我喜欢的鸟_第一课时(二等奖)(人美杨永善版二年级下册)_T644386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逢入京使》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安徽省
- 8.对剪花样_第一课时(二等奖)(冀美版二年级上册)_T515402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老山界》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安徽省
- 第4章 幂函数、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下)_六 指数方程和对数方程_4.7 简单的指数方程_第一课时(沪教版高一下册)_T1566237
- 外研版英语三起5年级下册(14版)Module3 Unit2
- 沪教版牛津小学英语(深圳用) 四年级下册 Unit 8
- 七年级英语下册 上海牛津版 Unit9
- 沪教版牛津小学英语(深圳用) 四年级下册 Unit 2
- 沪教版八年级下册数学练习册21.3(3)分式方程P17
- 冀教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第二单元《余数和除数的关系》
- 19 爱护鸟类_第一课时(二等奖)(桂美版二年级下册)_T3763925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老山界》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安徽省
- 沪教版牛津小学英语(深圳用) 六年级下册 Unit 7
- 每天日常投篮练习第一天森哥打卡上脚 Nike PG 2 如何调整运球跳投手感?
- 沪教版八年级下册数学练习册一次函数复习题B组(P11)
- 二年级下册数学第一课
- 沪教版牛津小学英语(深圳用) 四年级下册 Unit 12
- 冀教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第二周第2课时《我们的测量》宝丰街小学庞志荣.mp4
- 沪教版牛津小学英语(深圳用) 五年级下册 Unit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