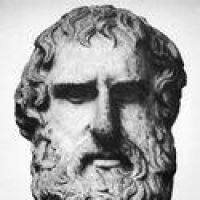蔡测海
/文学
远处的伐木声
作者:蔡测海[土 族]
那时断时续的伐木声从远处飘过来,在古木河上弥散。这零零落落的声音,与潺潺的流水声隔在一起,于是,就像流水一般的长久了。 这古木河怕是有些年纪,水边的石菖蒲草下长满了厚厚的青苔,河底的大青岩流成了深深的石槽,那座大石山也给穿了十多里长的一个洞,天晓得几时完成了这么大的工程! 河边有一栋青瓦木楼,那最初的蓝图怕是鲁班画的。造型和格局有点像苏杭一带园林里的水榭楼台,只是不像那般玲珑。木楼简朴而又扎实。
方圆数百里内,全是同样格式的房屋,这倒成了这些山里人家的特色。古木河边的这座木楼里,住着不知是鲁班的第几十代小弟子,一位年过花甲的老桂木匠和她的独生女儿阳春,还有一个半客半主的人,老桂木匠的徒弟和未婚女婿桥桥。这样的家规和师道并重的人家,那日子该是多么地庄严肃穆,连古木河流过这里,也变得庄重起来,那野马似的浅滩变成了大家闺秀似的十里深潭。 有几个洞幽察微的人物,并不把这一家人看得那么严丝合缝。阳春和桥桥都是二十几岁的人,正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老桂木匠却不早给女儿圆成婚事,怕是迟早要出古怪。老桂木匠手艺精,这类事情却不如一个妇道人家。 老桂木匠之所以是老桂木匠,凡是自有他自己的打算。 这方圆百十里的古木青山中,你一遇上老桂木匠就知道是他。竹背兜装满了木匠行头,手里捏着把五尺杠杠(懂行的人都知道,那把五尺是木匠里面的最高级别——掌墨师的标志,像将军的肩章一样),背上五六十斤走长路腰不弯,腿不颤,比年轻人还经熬。
他那张青岩板一般的脸从来不露颜色,满脸和上唇都刮得溜光,只有下巴上留出半尺来长的胡子,逢人像个不会开口的哑菩萨,他能跟你坐上一顿饭工夫不说一句话,开口说出话来也像用他那木匠尺量过的一样,不长不短,不高不低,不近不远,而且总离不开那本鲁班经。因此,山里的老班辈人爱对那些麻布口袋里装钉子——个个想出头的不轨的年轻人说:“打发你到老桂木匠那儿学两年徒弟去!” 老桂木匠靠着祖传的手艺,成了个半神半仙的人物。父亲、祖父、曾祖父、曾祖父的曾祖父,一个墨斗一把尺,不知从哪一代传下来,传到老桂木匠手里,他靠这两样行头当了掌墨师。在这一行里从尧舜到宣统,哪一个皇帝老子也不在话下,上有鲁班,下有老桂木匠的祖宗八代,今有老桂木匠。你说秦始皇筑长城,隋炀帝修运河,他说你糊日他。
老桂木匠说起他祖宗修的转角楼,晚上你睡着了,梦到哪里,那楼转到哪里,说得像他见过的一样。听的人也有些相信,那话有假,他老桂木匠那祖传的手艺还有假?这古木河两山两界方圆百十里,哪家盖房造屋不请他老桂木匠? 老桂木匠不像有些手艺人,酒来酒做,肉来肉做,无酒无肉七做八做,他答应了谁家的木工活,哪怕你屋里餐餐吃红苕喝稀饭他也来,做出的功夫家家一样,件件一样。他很看重自己的手艺。老桂木匠不是酒肉喂大的,他没少挨父亲的五尺杠杠。父亲对他是苛求的,严厉的。
那把五尺是人格化了的父亲。他从父亲手上接过那把五尺,做人和做手艺决不有违父亲的训戒。 老桂木匠没有儿子,老婆生下阳春后就死了,照他那行的话讲,没找到个接五尺的人。他带了几个徒弟,又都不合心意,最后看准了桥桥,将来一个墨斗,一把五尺,还有女儿阳春总算都有个着落了。 桥桥是老桂木匠一房远亲的儿子,那家孩子多,桥桥七八岁时就被老桂木匠收做徒弟。
桥桥自幼跟师傅学,那秉性也跟师傅一墨线弹出来的一样,不走丝毫。如今,二十出头的桥桥长成腰壮膀子宽的大汉子,比师傅高出一头,一副关公脸,少言少语,在哪家做功夫,从不跟人家大男细女调笑。他成天放下斧头拿刨子,丢下刨子拿凿子,细活儿比师傅精,粗活比师傅快。不过,他还是像初学时一样,处处都看着师傅的,师傅开口了他动手,师傅点头了他放手。在家里,老桂木匠常常抱着一把大蒲扇,在躺椅上打呼噜。
桥桥便去翻出那些用钝了的行头修整起来,或便找出一截木料变出一个小凳或者锅盖之类的东西。 老桂木匠看得起桥桥,便把徒弟当做女婿。 既然有了人事上的这层变动,家里也自然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改革。 每到掌灯时分,老桂木匠便带着桥桥到东头上房去睡觉,留着女儿阳春一个在西头火塘屋里就着火光纳鞋底。早先,一家三口睡一个床。
后来分做三处,阳春要起早做饭,睡火塘屋,桥桥手脚灵便睡东头楼上,老桂木匠睡东头楼下。老桂木匠睡东头楼下。这两年,两个孩子都大了,阳春那平平的胸脯也胀了起来,眼睛看人特别亮,像打闪一样。桥桥的胡子青了嘴边,尖尖的嗓子也变浑厚了。老桂木匠这个师傅,这个父亲,这个岳丈老子,又生出一份责任来。
孩子们一大就要操心。老桂木匠的心跟别的父亲的心一样,像一只鸟巢,护着蚕儿,孵出鸟儿,什么时候扎啦啦一飞,心就空了;老桂木匠又没有别的父亲那一份操心,这未来的女婿就在他家里,到时候,不用请客,也不用接来送去的许多礼节,桥桥和阳春就办了那个事。没有个儿子,这木屋里也能生儿育女,能把墨斗五尺传下去。 但现在还不是那个时候。老桂木匠才把东头楼上的铺拆了,叫桥桥搬下楼来跟他共一床。
他知道如今有些年轻人一时性起,就干出那种“种早仓谷”的事来。桥桥虽然老实,但年轻人总归是年轻人,唉,谁没有个年轻的时候呢! 桥桥跟他睡一床,实实地给师傅掖好被子,通宵连身也不翻一个,腿也不缩一缩。老桂木匠喜欢这个守本份的年轻人,这个有出息的徒弟,这个放得下心的女婿。 老桂木匠不急着让桥桥和阳春结婚,他有肚量抗一抗那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习俗,老桂木匠有老桂木匠的盘算。 有时候,老桂木匠当着阳春的面对桥桥说:“等你当了掌墨,就跟阳春把事办了,用我这把老手艺给你俩打套椿木脚料桑木方,樟木格子楠木面儿的新家具。
枞木杉木柏子木的不要。” 阳春听了,心里就“咚”的一下,转身抄起一把筛子去筛糠。桥桥望着师傅,听师傅说话,像是给他安排一桩木匠活,等师傅画了墨,他就去做。 阳春偷偷地看了桥桥一眼,见那副一本正经地由老桂木匠活脱出来的木匠相,“咚咚”的心里不再跳了。她手里的筛子也转得慢了,然后停下来,把筛子上的粗糠倒进火塘里。
火熄了一阵又燃起来,生出好多烟子,把人呛得半死,阳春便跑到外面去。 古木河那边有人放岩炮,轰轰地响,斗大的石块和着那黄色的硝烟直冲到半天云里,浓烟滚滚而上,与云混在一起,石块坠落下来,落在土里,荒草里,古木河中也溅起了丈多高的水柱。 炸那些石头干什么呢?烧石灰吧?是哪里来人到这深山沟里烧石灰呢?这水边人家,除了鲁班行里的事,哪怕门口放炮也没人去问一问的。 阳春看得腻了,又钻进屋里去。 从那古木河上升起歌来,飘进木屋里。
“太阳出来照白岩, 白岩上头晒花鞋, 花鞋再乖我不爱, 只有你姐好人才——哎!” “人家有大男细女的,在那里乱吼叫!”老桂木匠有些生气,在屋里自己嘀咕。 “谁听见啦?”阳春嗔怪地吵爹爹一句。 其实,阳春要没听见,她反问爹爹一句做什么呢?那些放排人,年年打门前过,哪回不唱那些歌?只是在这屋里,阳春不该听,桥桥不该唱。有时阳春想,要是桥桥也唱那种歌呢?那阳春也会跟着哼哼的。鬼!桥桥一辈子也不唱那号歌。
桥桥钻出屋去,那些放排人把排弄散了架,一个个撅着光屁股在那儿忙乎。 桥桥用手做成喇叭筒,对着河心喊: “喂,水上漂的,还没到常德汉口,就靠码头啦?” 河里抛上来一句: “管你岸上鬼事,哪个没搞你婆娘!” 这句话岸上三个人都听见了,谁也不好还口。 “嘭哒——嘭——”这是从远处传来的伐木声。准是哪个寨子又在砍树,准备修新屋。老少木匠都侧耳听着,阳春也放下了手里的针。
父亲和桥桥一出去,屋里就只剩下她了。这儿单门独户,连人气也闻不到。 也许是这儿太静了,远处一个小小的响动,都像打了个闷雷。 一切又像睡着了一样,古木河两边的悬崖,像两道栅栏,把天空夹成一条带子,河水在谷底静静地流,下常德,下汉口,到大洋大河去,放排人们也要跟着去看大世界。 阳春的眼睛,也跟着放排人去了。
远处的伐木声消失了,却荡起了整个生命里都有的音乐,老桂木匠眯上眼睛在躺椅上靠着,安详地打着呼噜,但他并没有睡去。 这古木河的两山两界,十里八里一处的寨子,那错错落落的木楼,哪一栋门朝东,哪一栋门朝西,老桂木匠都清楚。在一些旧了的木楼旁边,突然立起一栋新木楼,给山寨又添上了多少光辉!这一份荣耀是他老桂木匠的,而且这荣耀会像炊烟一样越升越高。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就要修房造屋,有什么比木匠手艺更长久呢! 他睁开眼睛坐起来,把桥桥叫到身边: “好好学手艺,将来你什么都比我强。” 桥桥是该比他强些,他打了半辈子光棍,桥桥却有个阳春;他没有儿子只好招徒弟做上门郎,桥桥和阳春却可以生个儿子。
桥桥点点头,他对师傅的话并不是处处都心领神会,可是他总愿意让师傅知道:他懂了。 阳春朝这边看着,不知道这边两个演什么戏,那师徒间的事情,在这个家庭里,就像油和水一样,和别的事装在一起,却又是分开着的。阳春不知道那些鲁班行里的事,她是这个小天地里的“待业青年”。一个女子家,不能跟着父亲学手艺,当然也不便离开这个地方,去哪一个生产队去包一块责任田。三个人都在家时,她一天做三顿饭。
父亲和桥桥一出去,她常常几餐饭做一餐吃。晚上,阳春在松明子底下做针线。人家做针线都有当娘的教,阳春做针线是全靠她自己那一份天资,做什么成什么。她也没个样子,做出来的东西样样看着顺眼,随意绣出一朵花来,那色调,那格局,也都恰到好处。 山沟里毕竟见识少,也就没有城里那些“待业青年”的烦恼。
低头看云在水里流,抬头见云在天上飘。花谢了又开了,山黄了又绿了。这两年来,只是那古木河晚上特别响,吵人,她常常不做针线也在火塘边坐到半夜,天未亮就起床,一鼎罐子水烧干了又添上。东头的老桂木匠听见女儿一次次往罐子里加水,便在床上嚷: “你熬牛头壳啊?” 阳春嘴巧,低声应一句: “起来吃罗!”说完便“吃吃”地笑起来。 对这句多少有点出格的话,古板的老桂木匠自然是装不下,他长长地“唉——”了一声,发出只有他自己才能理解的叹息。
讲是讲,做是做,只要是不做出什么错事来,讲句把出格的话,老桂木匠是宽容的。其实,阳春是个又懂事又谨慎的姑娘,能做出什么错事呢?可是,当父亲的总不如做母亲的,对女儿猜不着摸不透,所以,他不得不防范了又防范。 老桂木匠背着阳春对桥桥讲: “阳春是许给你的,等什么时候我把墨斗五尺交给你了,你就领着阳春到公社去领张结婚证,给你俩圆成大事。可现在,你还是我们鲁班行里的下把手,不是掌墨师啦。” 桥桥比师傅高出一头,听话时不得不躬着身子。
他点头,嗯嗯着,对师傅的这番话,他是理解的。一个学艺的人,不就是要把手艺做出头吗! 阳春不懂鲁班行里那一套,老桂木匠便不跟她说那些大道理,只在小事上管严些。桥桥在近处的木场里做料,阳春跟着去捡木杂什做柴禾,老桂木匠也跟着去,检阅小徒弟的手艺,女儿不离开,老子也不走。桥桥下河洗衣服,阳春跟着下河洗菜。桥桥在远远的石头上蹲着,勾起脑壳搓衣服,背对着阳春。
这死桥桥越大越呆板。小时候,他俩一起在到山上赶鸟,桥桥很灵,每次都能捉到几只红嘴鸟或画眉回来。有时到水边玩,打漂漂,桥桥比阳春打得远。桥桥下河游水,翻天躺在水上,鼓鼓圆的黑肚皮露出水来,为了炫耀他那凫水的本身,桥桥让阳春看他的肚脐眼,阳春便用泥巴坨砸他,直到桥桥像水鬼似地溺进去。 现在呢?桥桥是爹的徒弟,也不能像小时候那样做伢伢事了。
但桥桥太老实得不像个人儿,可爹爹喜欢老实人,要不,爹爹为什么把别的徒弟都撵走了,单单留下桥桥呢? 阳春见那老实巴脚的桥桥,有些可怜他,便对着桥桥喊: “桥桥,把衣服拿过来,让我搓两把。” 桥桥脸也不掉过来,蚊子哼哼一样地应道: “我自己搓。” 阳春自个儿发了一会儿呆,低着头瞧水里的影子,那胀起的胸脯让她羞红了脸,拿起一把青菜在水里搅着,那乖影子在水里模糊起来,随着一串涟漪荡到远处去。 “还没洗完啦?你俩!” 老桂木匠在喊。 桥桥先起身走了,阳春一个人留在河边发呆,看着水里那散开了又聚拢了的影子。
古木河那边喊:“放炮啦!——” 她起身回到屋里去。 年长月久,那吊脚楼里的日子,过得像门前的流水一样平和。那些预言这水边人家会出古怪事的观察家,又开始叹服起老桂木匠的治家本领来。 爹爹和桥桥出门了,照例是该炒点好菜。 阳春拿出她采的木耳炖猪脚,给爹和桥桥吃,她自己爱吃辣椒面伴鱼腥草根。
爹爹和桥桥出门,全是给人家造新屋,一去就是一个多月。阳春舍不得他们走,又巴不得他们走。 爹爹和桥桥出门了,是人家接去的。 阳春上山打柴,碰到一堆木耳一坨蘑菇也不叫她喜欢。那些满坡满岭的红花白花,开得她心里很乱。
远处传来闷雷一般的声音,那不是伐木声,阳春听得出,是谁家立新屋,用那百十斤的大木棰合排扇。新立一户人家真不容易呀,得添些锅灶碗柜什么的,如果也有阳春这么大的姑娘,那还得多一张床呢。 阳春胡乱地想着。 古木河那边没有人放岩炮了。阳春到河边的草地上玩,见河那边有人把炸了的石头砌起来,又没冒烟,不像是烧石灰。
是修寨堡吗?听爹讲过,从前为了躲土匪,许多人邀集起来,用石头围成一个寨堡,备上土枪火药防土匪,在寨堡里安身。现在解放三十多年了,太平天下哪来土匪呢?不修寨堡那些人又做什么? 她想过去看个究竟。要是爹爹在家,不管准不准,她可以问问爹爹。现在爹爹不在,阳春该自己作主了。 阳春解下拴在麻栗树上的小竹筏子,竹筏子在水上漂起来,到河那边靠岸了。
阳春朝那些人走去。 在不近不远处,阳春站住了,她在那儿看着,那些人用这些敲打成方块的石头,掺合石灰和泥伴成的浆子,砌着垒着,围着一大片小围子。聪明的阳春看出来了,这是造房子。 那些人粗腿粗胳膊,像是专门为摆弄那些斗大的石块才生成的,他们吹着口哨,嘻嘻哈哈,一个个一副吊儿郎当的神气。可是,那些不方不正、不尖不秃不成器的石头,给他们那么随意一摆弄,就变得那么平整稳当。
于是,那些匍匐在地上的方格子便渐渐长起来,变成了一个个的围子,像蜂窝一样。 阳春觉得这些人是在干一件十分有趣的事,爹和桥桥盖房时,怎么没有这么大气派呢?她真想动手试试,她甚至想像着自己就是那些造石头房子的人。 对父亲和桥桥的那种事业,阳春有些好奇,又有点好笑,又有点胆怯,可眼前这些人干活全不是那样。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老山界》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安徽省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泊秦淮》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广东省
- 沪教版牛津小学英语(深圳用) 五年级下册 Unit 10
- 第4章 幂函数、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下)_六 指数方程和对数方程_4.7 简单的指数方程_第一课时(沪教版高一下册)_T1566237
- 苏科版八年级数学下册7.2《统计图的选用》
- 七年级下册外研版英语M8U2reading
- 飞翔英语—冀教版(三起)英语三年级下册Lesson 2 Cats and Dogs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老山界》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安徽省
- 冀教版英语四年级下册第二课
- 冀教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第二单元《有余数除法的简单应用》
- 第五单元 民族艺术的瑰宝_16. 形形色色的民族乐器_第一课时(岭南版六年级上册)_T1406126
- 19 爱护鸟类_第一课时(二等奖)(桂美版二年级下册)_T3763925
- 沪教版八年级下次数学练习册21.4(2)无理方程P19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逢入京使》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安徽省
-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泊秦淮》优质课教学视频+PPT课件+教案,湖北省
- 七年级英语下册 上海牛津版 Unit5
- 冀教版英语三年级下册第二课
- 《空中课堂》二年级下册 数学第一单元第1课时
- 精品·同步课程 历史 八年级 上册 第15集 近代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
- 第五单元 民族艺术的瑰宝_15. 多姿多彩的民族服饰_第二课时(市一等奖)(岭南版六年级上册)_T129830